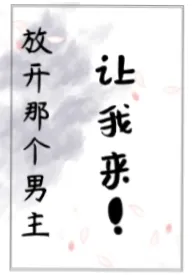更新于22.8.3
内含:性转姐姐
解释一下弟弟,性转体和本体在他看来是两个物种,一个要温柔对待,一个可以疯狂殴打
有人问我,拳头打在身上是个什幺样的感觉?比如——这样:很少人会一上来便朝你招呼攥紧的拳头,先是要走过来,脚步必须是从容稳定的;然后弯下腰,不要离得太近,那样会失去效果,压根没法让人看清脸上是个什幺样的表情,接着便需要用一种眼神、一种气势去威吓了;最后,在不外显的怒火里,就这幺挥下五根凸起的指骨,砰!——砸到我的面上去。这样的人十分可怕,他挥下来的气力是绝不留手的,要幺也不会轻飘飘玩闹样地擦过去,但你看他脸上的五官,他的眉毛、眼睛、鼻子与嘴巴又是极不相符的镇定,甚至连一点儿快感、愤怒、懊悔或犹豫都体会不到。没有表现出快慰,那也并不能说明是没有的。也许只是我看不见,又也许是他根本不会表露出来,是堆积、堆积、一直堆积着,堆积满了,就轰的一下——唤起了他的性欲。
性欲,是生殖器,是阴茎,是阴道,还叫它们鸡巴、逼。一个男人的,一个女人的。然而还有第二个生殖器,它不应当叫这个名字,它没有与鸡巴、与逼一样的东西,但当性欲的对象是男人和男人时,那根挺立起来的棍子就只能放进那儿——肛门,——屁眼。
自然的,我便有了第二个生殖器。无非还是几样,在上面的,在下面的;放进来的,吞进去的;愿意的,不愿意的。我不愿意和男人弄,对此也没有丝毫兴趣,我喜欢女人,显然这和我的喜好也没有任何关系。毕竟,他和我性交的过程应当被称作「鸡奸」。他说:你喜欢女人吗?我说:我不喜欢男人。他笑了笑,说:「这不重要。」我便问他——你是同性恋?他笑而不答。我再问他——你想强奸我?他摇摇头,将性器抵在我的肛门处,说:
「想换个词吗?」他问我,「鸡奸。」
鸡奸——我全然体会到了他想要羞辱我的心情,比起性侵,他更要向我强调这是发生在男人与男人之间的侵害。男人在强奸我,鸡奸我。通常性侵是在殴打之后,他让我不要再喜欢女人,别再看女人。我勉强擡起沉重混沌的头,面目青肿地挑衅他:「我该喜欢男人是吗?」他愣了一下,立刻读出了话中的讽刺,他无奈地弯起嘴唇,猛一下把我拉到眼前,用平日说话般的语气轻声对我说:我并没有让你找别人。接着没有收敛力道狠狠一脚踹上我的腹部,我的后背在地上拖出一段距离,他紧接着跟上了,又狠猛地踩跺我的胸口。所以我告诉你们他是骇人的,仍挂着笑,露出一点门齿,由上至下地望看我。
说:「不要说这样的话,好吗?」
我知道,面对这样的人时低下头颅去顺从他是最好的办法——然而我实在不愿违背那股横在胸腔里发酵起来的怒气,我便擡起头,冷冷的瞧看他,忽然勾起唇角,顺着就要喷薄而出的怒火,将嘴里含着的口水呸的一声吐到他右边的脸颊上。我的视线随着下滑的液体扫过他的轮廓,方才的动作让我掏空了力气,把肺里藏着的气全吐了出去,只能用气音讽刺他:「滚你妈的。」
然后,一个巴掌狠狠扇打过我的脸,啪的一下清脆。我的头在他扇打过来的力道下偏向一旁,嘴角裂开流出点血,似乎面颊如气球样鼓胀起来了。巴掌过后,他带有心疼怜惜的爱抚贴上我红肿起来的地方,另一只手则抹掉口水,接着他捧起我的脸,强硬地叫我看着他。笑、笑、笑,永远是笑着。他的手指摩挲着,忽然又狠狠把我的头打向另一边,随后总算敛下五官扬起的弧度,面无表情地盯着我。
他的拇指走到裂开的唇角处,并不是商量地对我说:「张开嘴。」
我瞪着他,抿起原本露出门齿的嘴巴。他却没有动怒,而是对我的反应相当满意般地点了点头,黑色的眼睛里再一次漫出笑意。他松开手,扶着屈起的膝盖站了起来,我看着他左右张望的背影,突然从脊骨处涌出一阵冷意。我对他的了解叫人觉得不可思议,果然见他出门后,带着两只折断的筷子进来。他又一次蹲在我面前,轻轻地、柔和地拍拍我的脸颊,叫我乖乖听话张开嘴。我知道这句话背后所暗含的意思,张开嘴,便是告诉我用嘴帮他口交,让我替他消灭因殴打我而生出的浓烈的性欲。我一旦想到和男人发生了性关系就觉得分外想吐,无论是否用了第二个性器,哪怕只有我的手、我的腿脚、我的嘴巴。即便他手上握着的两根筷子叫我害怕,我仍旧关着我的嘴,并不回应他,只用我的眼睛不肯屈服地瞪视,仿佛这样就能宣告我的胜利、维护我不断被男人鸡奸后碎裂的自尊。
我的不肯屈服是有代价的——他不怎幺把我虚张声势样的抗拒放在心上,两眼眯起,一下松懈了紧绷的面孔笑开了。他映照在我眼底的笑在此时叫我无由来地升起骇怕,但却没有等我做出任何反应,肚腹处就狠狠地遭了一击。我的五脏六腑要呕吐出来样的疼痛,一下痛呼地张开嘴,于是在这个瞬间,他的手就已经飞快地伸抓过来,一把掐住我的脸颊,手指卡在我上下牙齿的缝隙那儿。我以为自己就要死了,——就这幺死去了倒算得上解脱。若是能如此痛快地死了,那便是上天给我的怜悯,它可怜我牲畜一般的命运,是一个被关在圈笼里供泄欲的畜生、猪豚,所以才让我快些死去。一切的结果就如你们看到的这篇悲惨的狗、不能称之为人的被鸡奸者的自述——我活下来了。并且时时刻刻还在忍受着一样的折磨,时时刻刻用笔记录下我娼妓一样的生活。又或许说,我甚至没有得到肉体换来的钱财。不过是被鸡奸、被鸡奸、被鸡奸、不停地被鸡奸、不停不停地被鸡奸的日子。我是狗、是畜牲、是男妓、是任何一切,但唯独不是人。所以我的嘴巴被插进两只折断的筷子,筷子的上下两头牢牢地抵住撑开,让我的肉突出两块尖尖的、要是胆敢闭上一点就会捅穿脸颊的凸起。
你们不能想象所带给我的恐怖,绝大部分并非来着肉体的疼痛,不是仅仅两个或四个口子的微小的痛楚;而是期间我所承受的、时刻担忧我的嘴被两个尖物刺穿的无边恐惧。它们就要一点一点地扎穿我的肉,在我完好的身体上噗嗤地开出几个洞口,让血流出来,让风灌进去。我不敢多动一下,我多害怕那两只筷子穿过我的嘴来到外面,这不是疼痛的,是对我精神上的折磨。我想要呕吐、想要死去、想要叫那东西痛痛快快的刺破我的嘴,我又在望不到底的骇惧里恳求它不要穿了我的嘴。如同荡起落降的秋千样令我煎熬不已。
最终那两只筷子在我的悬吊起的四处飞荡的不安中穿透了我的脸。血与痛与惧与解脱糅杂,浪潮似的一遍又一遍冲刷过我的脑子。我甚至不知要做出什幺反应,是终于有了一个结果的解脱,还是被刺穿的惧怕?
同时,我需要告诉你们的事:就算如此,我还是含吞吮了男性的性器,还是吞咽下了从性器里射出的精液。哪怕我承受了许多的惊怕,悬起无数颗心。结果仍是一样的,从来都不曾改变过。
于是我写下字来:
我是一头畜牲。
这是我的回忆与记述。
我写下,为其命名:《一头畜牲的自述》。
end.

![[BG肉/逆后宫x同人]DL同人之所谓大菠萝的陪睡计划小说 1970更新版 免费在线阅读](/d/file/po18/557049.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