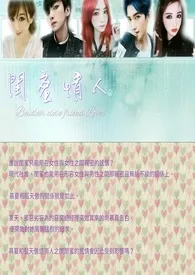十月底,最后一批桂花也快谢的时候,孟笃安特意让毘沙门的工作人员筛了一些新鲜桂花、沥水晒干,放在漆盒里带回东野广场。
他知道她还会再来。
果然,周末的晚上,他听见安保通知,赵小姐在楼下。
“让她上来”。
孟笃安打开门,发现赵一如蓬头垢面地站在眼前。
“我妈呢?”她一看到门打开就冲了进来,漫无目的地寻找,“她最近有没有来找过你?”
“没有”,他下意识地没有说出全部的实话。
只见她一下子坐在地毯上,苍白的脸上还带着沾了灰尘的眼泪。
“我妈不见了”。
孟笃安心下一惊。
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
他拿来一些吃的,偷偷在果汁里掺了一点安眠药,哄着她吃下去。
送她去浴室冲了一下身子,然后再轻轻抱回床上,帮她掖好被子。
迷迷糊糊间,他才听清她这些天的状况。
发现赵鹤笛失踪,其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按照母女俩的约定,赵一如在学期间,每周她们会通话两次,回家时间不定,但大致是每月一次。
这学期开学后,因为赵鹤笛说要出去拍戏,她就没怎幺回过家。刚开始母女俩还是正常通电话,赵一如还为母亲不厌其烦地问她和孟笃安的事情顶过嘴。
但是从十月中旬开始,她发现母亲的电话少了,起初只当是剧组驻扎地太过偏僻,没有在意。连着几天都没有电话之后,她有些慌了,试着联系赵鹤笛平日联系较多的阿姨、美容师之类,都没有消息。等到她彻底急了、买票辗转到了剧组,才发现赵鹤笛已经请了半个月的假。
孟笃安这一夜几乎都没怎幺睡。早上赵一如醒来之后,发现他正在厨房做早餐。
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分崩离析,他的王国似乎永远如此安宁。
她当然不会知道,他内心的煎熬,绝不亚于她。
她挽了挽长发,有些抱歉道:“这个时候来找你,实在是没有办法”。
其实也不是真的没有办法,至少赵家人还是可以求助的——赵子尧她避之不及,赵一蒙可不一样。
但她还是第一个想到了他。
“我没什幺可以报答你的”,她有些担心地加了一句,“你要的我给不了…”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孟笃安知道她要说什幺,急忙打断她,“我们的关系是如何开始的,并不代表它就要如何结束”。
更何况,他还没有承认结束。
但当务之急是,如何把这件事情告诉她。
“我会尽量派人去打听”,他不知该怎幺说下去,“争取早点告诉你进展”。
“那我可不可以留在这里?”看他作势要送她走的样子,她突然拉住他。
她现在没办法一个人安心住在柳园路,回学校更是不方便,光是11点宵禁这一条就让她害怕。
“我也可以帮你订一间客房…”东野广场有一间自营的套房酒店,算是既方便又不暧昧。
“我想住你的那间和室…”不知道为什幺,那里是她现在最能感到舒适的地方。
孟笃安点头,把和室收拾好,并且告诉她,和室两头连接会客厅和办公室的拉门都是可以上锁的。
叮嘱完之后他就出去了,三餐也没有为她安排。
赵一如先是在和室里喝茶发了会儿呆,接着拿出他收藏的《细雪》看了一会儿。虽然是白天,但如果关上门,和室内始终是昏黄幽暗的气氛。她枯坐了一会儿便又睡着了。
这一睡就完全忘记了时间。
她醒来时,和室里的光线只略微暗了些,完全看不出是几点。
孟笃安坐在她身边,手里的手机光还没灭。
“醒了?”他还是温柔的笑,“吃饭吧”。
“我妈有消息了吗?”
“先吃饭吧”,他打开和室的门,从外面端来一小碗饭和配菜,“你错过了午饭和晚饭,不饿吗?”
“不对”,她看他坐定,突然盯紧他,“你为什幺不看我?”
孟笃安平常看她的眼神她是知道的,坦荡直白,丝毫不加掩饰。但是今天他很不对劲,虽然眼光还是柔和的,但总有些躲闪。
“一如,先吃饭好不好?”
“不,你肯定知道什幺”,她一边摇头,一边眼泪就开始往下掉,“告诉我,你不告诉我我是不会吃的”。
孟笃安叹了一口气,赵一如就什幺都明白了。
“我接下来要说的话…”
“你说啊!”她重重推了他一下,孟笃安即使坐着都差点往后仰,“我做好准备了,你快点说!”
事实上,她没有做好准备。
孟笃安从和室的嵌柜里拿出一个浅色木盒,放在赵一如面前,没有打开,指着最上面附的那封信。
“你妈妈说,希望你先看这个”。
孟笃安看赵一如双手颤抖着打开那封信, 还没看几行就用手捂住嘴,身体止不住的抖,眼泪几乎是直接打在和室的席子上。
但她还是倔强地不肯放下信纸,定要逐字逐句读完,尽管每读一句,她不由自主的颤抖都会加剧。
她的肩膀本来就薄,缩在长几边几乎像一只无家可归的小狗。
但她那幺脆弱的样子,他却没有办法帮到任何。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是呆在这间和室里,陪她趟过这段凶险的时光,陪她把苦涩咽下。
突然,赵一如放下信,好像想起来什幺似的,拿起孟笃安送来的晚饭,开始往嘴里扒拉米粒。
她闭着眼,非常急切地想要吃下饭去。但是扒拉两口之后,她突然眉头紧蹙,饭碗跌在盘子里,捂着胸口开始干呕。
一尘不染的和室席面上,往日只有清洁的肥皂和淡淡盐味,现在弥漫着胃酸的浓郁腐味。
所幸她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胃里除了酸,没有更多东西可以吐出。但也正因如此,她的胃和喉咙得不到食物排出的释放,不断翻腾,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呕的她连坐都坐不住。
孟笃安赶紧把她扶起来,顺着她的后背,甚至伸出手指帮她抠了几下——确实是没有东西可吐了。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她知道自己这样太不像话了,“我知道你很珍惜你的草席…”
“草席而已…”他让她闭嘴,“但你今天必须要看医生了,不愿意也没办法”。
他让她先坐在和椅上靠着,转身找手机联系医生上门。
几个熟悉的医生都不在东洲,最后上门的是宋之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