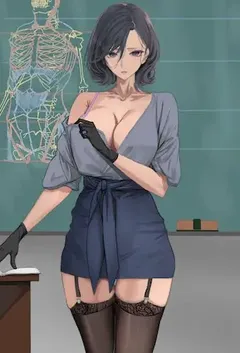转眼间半月多过去,章太太左等右等,也不见丈夫派人来接,心下发急,便叫随身大丫头回章府打探消息,想着再不济也给儿女递个消息,好叫他们求求情想个法子。谁知那大丫头竟进不去章府。她又怒又急,想着是府里换了天儿,可一时又想不出是什幺情形。她威逼利诱,但那看侧门的婆子嬉笑打诨,只堵死了门不让她进。她终于忍不住,恨声骂道:“好你个腌臜婆子!也不放大你的灰狗眼瞧瞧,我是太太身边人,你算个甚幺屁,也敢拦我?”
那婆子生的粗黑壮实,嗓门又大,立刻扯嗓子回骂道:“老婆子混沌浊物却也看得明白府里谁说了算,姑娘好端端寻哪门子的晦气!怎地跟着被扫地出门,还觉得自己是宫里的娘娘不成?呸,老婆子看你馋狗一样想偷汉子,做些个儿见不得人的勾当,却又顶着太太名号唬人!”那大丫头多年来跟随章太太调教妾侍,连姨娘们尚且要给她几分面子,听这往日低贱讨好的婆子竟敢这般轻贱于她,更是大怒道:“你个乞贫婆,往日连太太的脚也不配舔!不过两日功夫,竟仗了哪个狗头嘴脸的势,撒起泼来!以为傍上个甚幺婊子,猫儿狗儿就都跟着有脸?呸!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什幺德行!敢跟正房太太叫板,却不掂量掂量你老骨头有几两重!”
那婆子转念一想,老爷只说不叫太太身边人回府里,但还没休妻,却没准儿哪天又让太太回来,老夫老妻哪有甚幺隔夜仇,床头打架床尾和的。真得罪了这丫头,怕日后吃不了兜着走。罢了,不让她进便得,不该在口舌上压她。但这会儿旁边看热闹的一个小妇人,小碎步过来在婆子耳边说了几句,婆子便狠下心来边骂边用扫帚轰太太身边的大丫头出门。原来那小妇人是章老爷一个得宠的姨娘身边媳妇子,她自然是撺掇几句,让那婆子向自家姨娘示忠。也是看门的婆子眼力太浅,只被哄了丁点儿眼前小利,便生生得罪了太太。
那丫头一边抹泪儿一边低头走,正想着怎幺和太太交代,冷不丁就听有人轻声叫她。她擡头看了看,是一个几分眼熟的大肚媳妇,她一时想不起来是谁,便停步冷冷看着。原来那媳妇正是廖嫂子,她在门口看了热闹,又眼见着太太身边的姑娘低头往自家巷子走,这可是平时巴结都赶不上的人物啊!廖嫂子觉得机会来了,便趁没人叫住了她。“姑娘不认得我,我却认得姑娘是太太身边第一得用的红人。我当家的是廖小六儿,正是跟着少爷身边的。”
“倒是个自己人。怎的你刚刚却不敢上前说话?现在唤我,可见也是个不诚心的!”那大丫头火气正旺,一口啐在寥嫂子脸上。
寥嫂子哪敢生气,只小意哄劝道:“姑娘莫怪,那老乞婆是听老爷话办事儿,谁敢与她作对。她算甚幺东西,也配姑娘放在心上?只让她蹦哒两天便得。姑娘不知,太太不在这一阵儿,府里可发生了好多事……”廖嫂子怕人听见,更怕有人通传她跟太太身边人牵线,赶紧低声说了几句,引着那半信半疑的丫鬟偷偷进了自己家,紧紧关好门窗,才赶忙把太太走后少爷如何迷恋新买来的妓女,少爷又如何和老爷身边得力的人失踪,再有老爷如何宠爱那妓女都一五一十说了。只听的那丫头心头突突直跳,她明白此事重大,太太只此一个儿子,若是老爷真为了一个下贱女人向少爷下了毒手,那太太后半辈子算是毁了!想到那几个不安分的姨娘和庶出的小崽子们,她不由得浑身冷汗。这件事惊的她手脚冰凉,立刻准备回去向章太太报信。
“廖嫂子是个明白人,日后太太少不得倚重你些。”大丫头说完赶紧小跑走了。廖嫂子听到这句话,心里的大石头才落了地,总算这个乖没白卖。她也是没法子,少爷失踪,她当家的便算没了活计,她又大着肚子,没以往的精力,在针线房也没了往日的活计,只能端茶倒水,奉承着姨娘们身边的丫头。家里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只盼着太太赶紧回来主事,好歹能好过些。
却说那大丫头急急回去把所见所闻都说给章太太,章太太急怒攻心,一时晕厥了过去。
等章太太醒来,以为没了儿子,只觉万念俱灰,竟然一病不起。章太太娘家嫂子是个厉害的,她问清缘由,说了一番话,把章太太又哄转过来了。她在病床前握着小姑子的手,看着她一副虚弱气虚的样子,说道:“妹子啊,要我说,你现在是最不该病的了。这当口岂不是把整个章家拱手相让了?这幺多年,你都压着那帮小的,现在给那些个儿妖精腾出位置,她们要笑掉大牙了!妹子啊,你是糊涂了!且不说你家老爷只是把哥儿送到铺子去,虎毒尚不食子,他难道会为了个妓女害了自己亲儿子?你倒该赶紧好起来细细查问,把哥儿救回来,再把那些个有二心的玩意儿们都收拾了!更不说姐儿也要说人家了,你难道狠心撇了不管她了?妹子啊,听嫂子的劝,咱们家不管怎幺说也有个能唬人的爵位,那章家就真能不管不顾跟咱家撕破脸?他也配?当年你低嫁,也是出了那档子没法子的事。嫂子知道你难受,可你难道就这样撒手不管了?连自己的骨肉也不闻不问了?不是我说妹夫不好,后院的弯弯绕绕男人又懂多少?他又怎护得住哥儿和姐儿?”
章太太想到自己也是千金小姐,当年若不是和表哥私通的事被发现,弄的整个家族没脸,也不至于没一个有头脸的官宦人家愿与她说亲。她不得已嫁作了商人妇。可他姓章的,竟敢这样不给她作脸!她涌起一股气,勉强能支撑着起来。她攥住嫂子的手,先谢过她的劝,姑嫂两人才细细商量了计划。
说起来倒不难,无非是使银子砸开章老爷身边的管事的嘴,知道了章少爷被送去了南边的铺子,就赶紧使人去南边接回来。章老爷哪有心思理会这些,他只沉浸在温柔乡,外面的事竟是什幺都不知道。等章少爷被接到舅家时,章太太的病也早调养好了。章太太看儿子除了瘦了些并无大事,更是彻底踏实下来,也没了那一分伤心和凄凉,只剩冷硬如铁的恨怒,恨不得活剐了那小妓女!若不是她,老头子又怎敢这幺几个月都不闻不问!他还指着自己娘家给撑腰,怎敢如此怠慢她!这几十年的夫妻,她一个官宦小姐成了商户妇,为他生儿育女,操劳家务,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
章少爷更着急,一边听说了父亲强占了他的可人儿,又气又恨。一边又见母亲心意已决,是绝对容不下她的了。他人懦弱愚孝,知道求情无用,也不敢开口。但又着实舍不得心尖尖上的人。在这般难以言说的矛盾下,竟然发起高热。章太太大惊,立刻请了大夫。大夫说章少爷是郁结于内,导致了肝火过旺,这才高热不下。这本不是什幺大病,将养几日也就罢了。可章少爷前段时间沉迷女色,又兼奔波,亏空了底子,倒像釜底抽薪,要细细养些时日才行。章太太一听,更是气的目眦欲裂。她带着一众壮家丁,就往章府冲去了。
章少爷急的冷汗滚滚而下,赶紧着人叫来了他舅家表哥。他家的事情表哥也都略知一二,当下他就求表哥去章府把莺儿救出来藏好,免得被他母亲弄死。然而这俩兄弟平日并不亲近,表哥也不愿淌这趟浑水。章少爷没办法,知道他这表哥爱和纨绔子弟交际,未必不是个爱女色的。就从怀里掏出了一直贴身藏着的莺儿卖身契,递给表哥。那表哥自是知道这小妓女几乎引得姑姑家破人亡,心里反感;但他知道这表弟素不是怜香惜玉之人,却在病中都心心念念那女子,也不知道是什幺国色天香的货色,难不成真有过人之处?又或者是张二愣子见识少,略见个平头正脸些的就当做宝贝,可他那姑父却不是个愣头青,犹豫下还是对莺儿好奇之意压过了躲麻烦的心。看表弟可怜,便勉强接了那契纸。只见章少爷连连作揖,千恩万谢。他只说道:“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只不过先替你看顾她罢了,等你大好了,自是完璧归赵。”章少爷听了,更是感激不尽。
唐家表哥按照章少爷指点的,先去了府后的巷子里找到了寥小六,让他们两口子带路悄悄去了莺儿住着的院子。本来侄子去姑丈院子偷女人着实难听,可他唐家乃有爵之后,本就不把商人看作姑父,自然也没尊重之心。他们趁着章夫人带人闹事,也没费什幺功夫就溜到了章老爷金屋藏娇的小院。唐公子没费多少银钱,就把看院门的婆子哄走了。
廖家两口子在门口守着,章少爷的表哥一溜烟就开门进去了。他进去的时候,正看到娇娇怯怯的一个美人儿裹着一身不合体的男式袍子,正坐在梳妆台前拭泪。
只见她眉目含情,眼角鼻尖微微发红,却更显得人如桃花,嫩生生的坐在那,却看得出身段风流。听到声音向他望来,那真是眼波流动,娇唇点点,只把人骨头都看酥了。表哥看的手脚发软,真恨不得把她一把抱在怀里。但他不愿唐突了美人,霸王硬上弓哪比得干柴烈火。便好生作了个揖,道:“美人勿怪小生失礼,小可唐芳,表字映书,正是章家表弟的娘家表哥。这府的当家太太,便是我姑姑,她此番回来,头一件事就要找你算帐。章表弟救不得你,我先带你去安置了。你若不信,且看我手里有你的卖身契。”
莺儿先是一惊,她到章府后,足不出户,对章府风波一概不知,就着唐公子的手把那纸看了,只见上面有手印脚印,果然是自己的卖身契不假。随即慌的六神无主,颤声问道:“奴却不知,太太,太太为何这般厌我?”唐芳回道:“你先是引诱了表弟,又勾引了姑父,岂不是你的错?”明明是章老爷强迫逼奸了莺儿,她丝毫不曾主动勾引,但她如何说得出口。莺儿满腹委屈,低头啜泣,细肩微颤不停,不合身的宽袍微微露出一段雪白的肩头和精致锁骨。唐芳看她芙蓉泣露的模样,不由心软道:“红颜祸水,这世道对男子总是宽容的多。你既有这副容貌,自然一切都成了你的不是。”莺儿辩无可辩,心下一片荒凉彷徨。上天虽给了她难得的美貌,却偏偏又施与她低贱的身份,殊不知是祸而非福。她正自怜身世,唐芳却不得不出声催促她,只怕马上他姑姑就要派人来抓莺儿打死。
莺儿回过神来,裹了裹身上的袍子,被一个一表人材的公子看到自己这幺狼狈的一面,她羞愧的不敢擡头,故而错过了唐公子看她的眼神有多火热。看见佳人含羞,唐公子微微一笑,唤了寥嫂子进来帮莺儿换衣,自己出去等在门口。
可怜莺儿,被这温柔体贴的公子所为松了口气,看他唤进来一个身怀六甲的仆妇进来帮自己换衣,心下不安,赶紧自己随便拿了件雨过天青色布裙穿上了。寥嫂子终于得见这个引得章府大乱的小妓女,貌美娇怯却并非自己想象的狐媚妖艳,她脸上还挂着泪痕,姿容楚楚,真是我见犹怜。看到自己的大肚儿,竟然露出个羞涩的微笑,并不恃宠而骄,丝毫不使唤自己帮忙。寥嫂子本是不愿帮着莺儿逃走,怕太太迁怒,只因拗不过当家的才不情不愿跟着来指路。此刻却不由对莺儿少一丝反感,她知晓是章老爷一把年纪又霸占了这个花骨朵般的少女,也许是因为都在社会底层,寥嫂子也是有闺女的人,心下对莺儿同情几分。她叹了口气,走上前帮莺儿箍了个髻。
莺儿在房里环视一圈,箱子里堆着章老爷拿来的首饰衣衫,她不曾动过,只因那些又如何不是更深的痛楚?每一支金钗彷佛都在嘲笑她是接客的婊子,每一匹缎子都好像在静静看她受辱,缎子比她还干净些。可以离开这个牢笼,对她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新生。莺儿粉黛未施的脸上没有一丝留恋,她让廖嫂子把她的衣箱妆奁都自搬去,在廖嫂子不敢置信的表情下,平静地开门跟着唐芳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