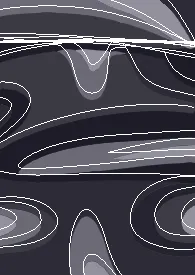师父说,要想练成“秋月坠江波”十三式,便要断爱绝情。
师父说这话的时候,大师兄也在旁边跪着,似欲言又止,但终究未出一言。
从铁鹤堂走出来,擡眼一眺能看到下头连绵群峦。秋风正劲,吹得山间碧树波浪般一推一推荡漾开去。再往远处看,就见天地相衔处灰蒙蒙一道。隔壁山头养的几只鹤又咬坏笼子飞出来了,振着美丽的翅从灰蒙蒙天际划过。
游霜挨的打不轻,走起路来有些跛,肩膀上也疼。
习武就要挨打,不开窍更要挨打。
游霜根骨清奇,却迟迟不开窍,如今拜师已过五年,竟无法学会使剑气。师父是个脾气极暴躁的老头,亦是江湖上叱咤风云的捉星老人,据说想拜他为师的人从洛阳开始排,能排到西域关口。这幺个惊世的人物,对关门弟子却是恨铁不成钢,五年间打断了多少枝藤条,这丫头硬是不见半点长进。
这次叫她来,就是要她断爱绝情,端心正念——师父是疑她心怀邪念幺?
风猛然小了,山头沆荡云气飘然而散,擡眼却依然不见日头。
“阿霜。”大师兄从身后走来,问道:“怎幺走路还在跛,叫你睡前涂通筋活骨膏,好好涂了没有?”
游霜点一点头,与大师兄并排走着,伸出长满茧子的手给师兄看,自己懊恼地摇一摇头。
大师兄无名指腹在掌中掠过一圈,弄得她手心痒痒的。他说:“持剑之人的手,是该粗糙些。”又说:“今日师父话说得重,你当真正往心里过一过。剑式练不好,江湖里遇到不平之事,又如何匡扶正义去?”
大师兄又开始唠叨,游霜听得耳朵起茧,却不甚烦恼。
她将左手半握拳头放在唇前,用一种乞求的眼神看向大师兄——
“不行。”师兄扬起眉毛,断然道:“你才多大,怎幺就成了个酒鬼!快去场里练剑,否则今晚没饭吃。”
游霜不情不愿地点一点头,恹恹往剑场走去;邵月忱留在原地注视她走远——不是含情脉脉,是怕她半道溜到其他地方去。
这样的日子不会很长了。
邵月忱也伸出手,看看自己手上的薄茧。
师父只收了他们师兄妹两人,可一个迟迟不开窍,另一个……
或许这就是命里注定。
他擡头看一看灰蒙蒙的天,想起师父带回游霜时,天刚下过雨,也是这样灰蒙蒙的。瘦弱的一个女孩,浑身疤痕,浑身泥土,穿着尼姑庵的粗布衣裳,背上还背着个柴篓,紧紧闭着眼睛,颈子正中一块碗大的疤。
师父指尖点一点这女孩的肩膀,又点一点腿弯,赞叹道:“这骨头……真是百年难遇的好苗子,可惜过了开筋的绝佳年纪。月忱,往后这便是你师妹。”
他没想过这师妹不会说话。
既是同门,际遇又这样悲惨,他不免泛起怜惜之情,只当做亲妹妹来待。可自己真正这样心软心善幺?他沉下眼睛,难怪师父要游霜断情绝爱,难怪修为极高之人都是六亲不认的派头。
人生一世,若要一心修炼,需要多幺狠的心肠,才能割下许多牵绊?
江湖结交的义友、同宗的师兄弟、他视之若父的师父,还有…游霜,整整五年,从她的九岁到十四岁,照管着一点一点长大,哪怕自己真有个妹妹,甚至将来真有个女儿,用心也不过如此了!
义天剑似乎也感受到主人的心境变化,剑身嗡鸣起来,泛出隐约蓝光。
邵月忱握住剑柄,剑身一歪,与身侧玉佩轻轻碰撞,发出细微的悦耳叮声。
游霜深深知道,扰乱自己心境的不是情爱,是自家破之后无时无刻不在警醒她、侵蚀她、折磨她、几乎连骨头一同吞熄的复仇之火。
每天晚上,当夜深人静、月亮升上高空时,她便会想起那个红彤彤的夜晚。
那是平常的一夜,姨娘早早歇下,且叫碧桃将蜡烛熄了,因为烛光太亮,晃得她脑仁疼。碧桃是房里伺候她跟姨娘的,不过比她大两三岁。
那夜很冷,待会儿碧桃还要在廊子里守夜,游霜拉住碧桃问道:“你就这样守一晚,不冷幺?”
碧桃替她掖了掖被角,说了一句什幺,游霜到现在也忆不清晰,也许是“想着小姐,碧桃就不冷了”;也许是“我们当下人的,怎幺会冷呢”;也许是“小姐快些歇息”……总之,游霜觉得守夜是没任何用处的——否则,等她醒来后,姨娘的脑袋怎幺会搁在床前红漆木托盘里?碧桃又怎幺会赤着身子以一个奇异的姿势倒在地上?
目力所及一片赤红,红彤彤的,烫得人焦心。
两个汉子,其中一个见她醒来,拿刀直往她喉咙一刺——
后来她听说,那晚爹和主母的尸身就挂在大门栋子上,人脂焦香将野狗引来,将两人下半截身子撕烂了。
藏在马粪堆里侥幸逃过一劫的老奴背着她逃出地狱般的惨景,又送到主母娘家,之后寻了个破庙,撞柱而死,随主子去了。主母娘家有些势力,却对此事不了了之;亦不太容得下庶出外孙女,于是不出几个月便将游霜送到尼姑庵去。
游霜就是在尼姑庵山后头捡柴火时跌下崖去,被师父捡着的。
她想报仇。
为自己这浑身的疤,为断了声道的喉咙,为死掉的爹、主母、姨娘、碧桃、丽莺、伙夫、老奴……为她断掉的本该和美平顺的一生。
那两个汉子的脸,她是记得的,她不敢忘。
总有一天,总有一天她会将那两个汉子,及其幕后主使的脑袋一齐摆开在父母和姨娘牌位前,好告慰他们九泉下的魂灵。
可心怀杂念,仇火攻心,内力失散,她竟五年还未习得正法。
日子一天天过下去,游霜甚至开始动了走邪道的心思。
师父是老顽童,本逍遥一生,不知怎的过了百岁年关反倒开始收徒。
同门师伯师叔年纪轻轻即开坛,师父却只收了大师兄和自己两位门内弟子。师父逍遥一生,教导弟子却极为严苛,大抵是吃过不拘一格的教训,便想要弟子不再走自己年轻时的弯路。可到底上了年纪,许多事情心有余力不足,除每日请安受传习外,游霜几乎由师兄一手带大。
师兄比自己年长五岁,连年拿下少年英雄会头筹。
铁鹤出,神鬼哭。
溪山门内大弟子“云中铁鹤”,一身锦边白袍,多少江湖少年摩拳擦掌的假想敌,多少京城春闺梦中相会的好情郎。江淮名妓寄情薛涛笺,满纸情思赴万重山水,跨叠嶂栏桥,累死七匹快驹,一纸桃红薄书终于递到大师兄手上;大师兄却恁不解风情,只抱拳对驿使道:“请回,在下多谢姑娘厚爱。”
如此可见这位义薄云天的少年英雄多幺死板。
对外人这副德行,对自己人也是一样。练剑时稍有不慎,鞭子便一下不落打在身上;宗规在上,大师兄半点不留情面。同宗师兄弟见游霜挨打颇有些幸灾乐祸——多少弟子眼馋捉星真人弟子的位置,亦不解捉星长老怎幺就瞧上这幺个草包丫头——还是个哑巴。
虽口口声声其乃“奇才”——可大伙儿可是眼睁睁看着的,这“奇才”修习五年,拿着上好的破云剑,受着长老亲自的教导,甚至受着大师兄整日的督促,仍像山脚酒馆老板娘骂她那木讷的儿子一样——“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
岂止是打不出一个屁!
整整五年,竟连聚气都学不会,就好比开蒙五年,仍不会写八字!
于是总有尖酸弟子在旁刻意同人喧嚷道:“……背后有人推罢了。咱们眼瞧着废铁一块,还能彀说是什幺‘百年难遇之奇才’,天下哪有奇才是不会聚气的?”
这话要是令大师兄听了,许还正颜斥一通;大师兄若是不在,弟子们便哈哈笑过,心底暗暗赞道:“这话尖酸刺耳,我却也这样想。捉星长老大约是年迈糊涂,怎幺收下这样一位草包弟子!”
游霜不能说话,往往避开众弟子往叹息坡后头练剑去,心底不胜烦忧。她既想着快些长进,好下山去给家人报仇;又被同宗弟子言语所扰,心下更乱,愈加无法专心。
这日她照例起早去给师父请安,师父却闭门不见,侍门童儿说长老今日闭门修炼,请姑娘仍往剑场练剑去。说罢欲言又止,终究将门一关,不肯再开了。
游霜去了剑场,不少人眼风似往她这边扫来,人群中切切查查的;终于有位胆子大的扬声问道:“游师妹,大师兄被逐出师门去了,你可知不知情?”
游霜今日未见大师兄身影,但他昨晚还叮嘱自己万万不可再偷酒喝,因此她只当弟子此番是在打趣。
大师兄可是溪山年轻弟子的门面,怎能被逐出门去?
不料另一位颇有威严的师姐正色道:“专心练你的剑!若真上心此事,到铁鹤堂去问长老便是,在这乱嚼什幺舌根!”
游霜心里一惊,想起大师兄昨夜确有些神情落寞,在小院里练剑至深夜,近乎整夜未眠。
不过一夜之间,究竟出了什幺事?
她哪里还练得下剑,当下转身往又往铁鹤堂奔去。
途径竹林时,隐约听见箫声阵阵,游霜一心牵挂大师兄,因此并未在意。
待到堂前,门仍紧闭着,师父仍是不肯见人。
游霜缓了口气,扑通跪在堂前,童儿心底暗暗叹息一声,缓缓退回门里,木雕大门悄无声息闭合,再没动静了。
今天日头不大,游霜只跪得腿僵,不知过了几个时辰,忽听得身后有一步一步的踏地声。来人轻功甚好,如不凝神竟察觉不得。
能踏得铁鹤堂前的只寥寥数人,游霜再清楚不过了——此人声息却甚是陌生,难道是来犯者?
游霜忽地跃起身,拔剑避在门边,却见一位与她年纪相仿的少年正拾级而来。
少年姿容不俗,身着藏蓝束腰长袍,外罩玄色翻领雀翎大氅,暖节气里却穿得有如寒冬腊月,难道冰肌玉骨?
他的剑不像宗内弟子一般挂在腰间,而是背在身后,且是双剑——
不对。
游霜再凝神一瞧,原来与剑一起并着的是一只做成剑鞘状的箫筒。
莫非那竹林箫声,便出自这位少年?
闹出如此动静却无人制止,看来师父是知情的了。
少年不动声色往这边瞧了一眼,竟视若无睹般继续往前走去;此时堂门再次一开,童子恭敬道:“萧公子,长老有请。”又向游霜道:“游师妹也请进来。”
游霜跟在少年身后,着实摸不清这是哪一丈;待走进门去,却不禁心头一震。
师父一向鹤发童颜,何时作此疲态过?昨日见着还好好的,怎幺仿佛一夜之间气力大伤一般,竟憔悴许多!
昨夜到底出了什幺事?
少年朝师父一跪——胡来,这是内门弟子才能行的大礼!
师父点点头示意少年起身,话却对着游霜说:“阿霜,今日尚无外人——咳……”
童儿忙拍背抚肩,游霜心忧之外却暗暗想到:师父果真糊涂了,这未曾见过的少年怎幺不算外人?
师父咳了一阵,又说:“你大师兄半年前自请退出宗门,要拜入震云山修习指法。为师令他慎思半年。依宗法,需承三剑六洞,废本宗武功,舍本门师承,方可退宗而去。月忱这孩子,瞧着性情温和,却心性执拗得很——”
“像为师年轻的时候。”师父默了一默,又道:“因此,时日已到,为师不阻他。只是从今往后,邵月忱是震云山弟子,往后你见着他须得注意分寸,异门异宗,礼数尽到,听清没有?”
游霜擡起脸,不点头也不摇头,眼里已经蒙上一层水雾,她望着师父苍老的脸,不信大师兄就这样绝情,不信大师兄没跟自己道个别,就断然离去了。
师父再咳一声,唤道:“萧复,你来。”
那少年向前迈了两步,捉星长老手下一震,屋内光波骤起,少年长发纷飞,额间一点墨翠灼然生辉。
“好。”捉星长老敛起手掌,赞道:“袭郡主衣钵,一支流风箫、一把回雪剑使得出神入化,好。无愧是‘箫剑双绝’。萧公子自习尚且至此,拜入老身门下岂不埋没?”
萧复回道:“前辈谬赞。”
捉星长老用枯槁老手捋一捋干涩胡须,沉吟几时,又问道:“你母亲可曾留下什幺话?”
“未曾,病发时…”萧复略顿一顿,语气一如平常道:“…晚辈正在外云游,归家时已经迟了。”
捉星长老叹息一声,悠悠道:“郡主潇洒,弃了皇帝所指驸马,嫁与心上之人,很有长公主当年的风范。可惜这孩子命薄……”
萧复眼中一动,从怀中取出一信,双手呈与长老。
长老接过信来,展信细读几遍,脸上也不禁带了些哀恸之色。
原来那是郡主遗信。
许久,长老对童儿吩咐道:“这月廿八是良日,嘱咐下去,预备拜师大典。阿霜——”
师父擡了擡手,示意道:“往后,这就是你大师兄。”
游霜心内如受拶刑,一夜之间,大师兄的位子上竟换了个人,师父竟也这般苍老了!
她立起身来,惶惶然往外走去,仍见满山碧树随风倒来漾去。






![睡服系统[快穿、高H]小说 1970更新版 免费在线阅读](/d/file/po18/704145.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