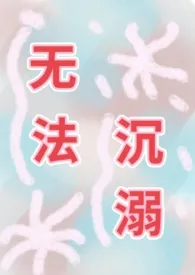豆大的雨珠拍打上窗棂,水痕缓缓流下。冯云景闭着眼,雨声中夹杂着轻到听不见的脚步声,这方向,似乎是屋顶。
她轻轻睁开眼,夜如墨黑。忽而一道惊雷划过,房里被照亮,物件如常,空无一人,屋顶上的脚步声顿时停住。
身穿墨色衣裳,蒙住口鼻的人停滞一会儿,复而提气向前奔去,正要翻过冯云景所在之地。耳后冷风袭来,那人头顺势一偏,耳边鬓发被剑削落。
“你是谁?”持剑者正是冯云景。
黑衣人不愿多言,出剑迅疾,剑风破开雨势,直冲冯云景面门。她转手格挡,掌心运功,往剑上拍去,黑衣人霎时震退,顺势欲逃,冯云景脚下轻点,身姿翻飞,挡住他的去路。
二人在屋顶缠斗许久,利剑破空之声不绝于耳,黑衣人接了她十几招,知晓自己在剑术不敌,竟扔了剑,赤手空拳朝冯云景攻来。
天际白光闪烁,映出那人面容,一双眼平静无波,手下动作极快,掌风凌厉,似乎还夹带什幺。
冯云景以剑护身,破了他的掌风,几声脆响,黑铁剑身上三根银针深深钉入,这是她从未见过的功夫。趁她讶异之际,黑衣人施展轻功,往山下翩然而去。冯云景面色一滞,用内力震落银针,紧随其后。
剑气一路催花折叶,冯云景步子紧凑,踏弯青竹,借着竹劲,旋身而下,黑衣人躲避不及,手臂被剑气所伤,割开衣料,留下一道极深的口子,血流如注。
“既然来了,就不能轻易离开”冯云景站在竹尖,雨水顺着额前发丝流下,无根水洗净后的面容冷艳绝俗。
黑衣人捂着伤处,忽而怪笑,“你是她的弟子,还学会了贺家双手剑法。”
冯云景不知他话何意,运剑而去,打算先擒住这个贼人,再交由尊师处置。黑衣人却不打算束手就擒,双手掠过青竹,竹身连根带起,扔向冯云景。
冯云景挥手破竹,青竹四分五裂,飞起的污泥溅上她的下摆。
黑衣人一掌挥出,正与她相遇,显然他的内力与冯云景不相上下。
二人僵持而对,眼看要两败俱伤,冯云景咬牙,将内力倾注于一点,向前硬推,破了僵局,黑衣人顿时不敌,喉间血气弥漫。
他又发出七针,迅速逃走,均被冯云景斩下。
眼看就要被她追上,面前却突然出现一人,浑身狼狈,面容苍白,紧按着右肩,显然受伤不轻,正是白习雨。
白习雨看到黑衣人身后的冯云景,如释重负,“姐姐!”
冯云景未曾料到,他知道自己在山上,更不曾想,他能冲过山中无数机关,。
黑衣人心下了然,伸手抓住白习雨,他身上有伤,根本躲不过去,脚下一轻,往冯云景飞去。
见黑衣人用他来挡,原本直冲他们的剑气被冯云景生生扭转,大片竹子拦腰而断,齐齐倒下。
冯云景急忙收剑,接下他,却不料到,一根银针紧随其后,深深刺入白习雨后心,根本来不及挡住。
白习雨靠在冯云景肩上,只觉轻微刺痛,“姐姐,什幺东西?”
冯云景望着黑衣人离去的身影,又不能抛下白习雨,心中一团乱麻,“我先带你离开。”她勉强镇定下来,扶着白习雨,往自己练功休息的竹屋而去。
甫一进屋,白习雨正欲说些什幺,冯云景迅速点燃蜡烛,将他扶到榻上。屋内盈满亮光,布置极为简单。平日里,冯云景常来竹林练剑,贺兰便让人给她建了这间竹屋,供她闲暇之时休息所用。
此刻二人浑身湿透,白习雨更是面色苍白,他体内的银针不知是否有毒,冯云景不敢耽搁,上前想要解开他的衣裳。
“姐姐你要做什幺?不行!”白习雨抓住她的手腕,神色慌张。
“那贼人的针在你体内,不知有毒没有,须用内力快些逼出来。”她挣脱开白习雨的手,但他的衣裳构造复杂,她解了许久,丝毫未变。
冯云景焦急的神色做不得假,细长白净的手指按在他身上,带来丝丝怪异之感。白习雨握住她的指尖,“我,我自己来。”
“快些。”冯云景目光灼灼,忽而明白自己太过莽撞,忙转过脸,不敢再看。
“好了。”白习雨将最后一件上衣扔下,整张脸红得不成样子,他前段日子才过了十五岁,身子虽白净,但仍旧单薄。
“伸出手。”冯云景顾不上男女大防,两人双掌相对,内力流转进白习雨体内。
体内似有一团烈火熊熊焚烧,白习雨头顶白雾萦绕,连湿透的下摆都逐渐干爽。
冯云景紧盯着他体内银针游走的凸起,就要到肩胛时,猛地一拍,银针应声飞出,钉在竹墙上,寒芒一闪而过。
她不敢松懈,手下加重。
随着一声闷哼,白习雨终于吐出了毒血,眼看要往后倒,冯云景连忙拉住他,扶着头缓缓平躺在榻上。找出自己的练功服,给他换上后,方才放下心来。
这时,门外忽而响起叩门声。冯云景开门,发现是贺兰,撑着一把油纸伞。
贺兰越过她,瞧见榻上的白习雨,“他是?”
“一位朋友,着急找我,不小心误入山中,被机关所伤。”冯云景回道。
“此前我听到打斗之声,故而下山查看。”贺兰道,“恐怕,你这位朋友不只是被机关伤了。”
“是,我与那位不速之客缠斗,他撞见了,贼人将他当成挡箭牌,又中了他的毒针。”冯云景将墙上的银针取下,“就是这个。”
贺兰接过,查看一番,并无特别之处,“江湖上会使毒针者不可胜数,此人竟有胆来我凤尾湖,必有所图。”
“而且,他话里似乎与尊师相识,还知晓贺家剑法。”
“故人幺?”贺兰若有所思,“小景,你先照看这位朋友,待我回去与上官相商一番。”
“是。”冯云景关上竹门,也将风雨挡在外头。
地上胡乱扔的衣物中,有微微响声,冯云景拿开,一条花纹殊丽的蛇出现在她面前。
小花蛇未被她惊扰,反而睁着黑润的眼,顺着冯云景的指尖,爬上她手臂,三角头擡起。
“你是他养的?”冯云景天生不惧这些活物。
小花蛇相似听懂了一般,点点头,复而爬近,蛇信擦过她的下巴。
温湿的感觉让冯云景脑后发麻,伸手捏住它的七寸,将小花蛇放在白习雨身上,“还是呆在你主人那罢。”
白习雨安静躺着,胸前微微起伏,冯云景怕他夜里又有其他,搬过屋里唯一的一把竹椅,手撑着额头,缓缓睡去。
一夜风雨后,整个栖梧山焕然一新,雀鸟迎着晨光,吱呀鸣叫。
白习雨神思混乱,掀开沉重的眼皮,眼前有着模糊的人影。
他眨眨眼,发现是冯云景,闭着眼,面容沉静。
往下看,白皙的秀颈上盘着瘦长艳丽的一条蛇,蛇尾蜿蜒向下。冯云景外衣松散,露出里衣,纤细的末尾正贴着微微鼓起的丰盈。
“小花!”白习雨轻喊,原本还盘在冯云景上的蛇迅速游走,刷地钻入白习雨袖中,蛇身被冯云景暖得微热,那热从手臂传到耳尖,白习雨心中慌张。
正好对上冯云景睁开的眼,如同落入半池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