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听眠成了秦枝意名义上的秘书,领着一份和市场价不相上下的薪水,每天要做的却只有呆在办公室里看她批阅文件忙到擡不起头,顺带着在闲暇时满足一下老板的某种需求。
沈听眠可体会不到做金丝雀的乐趣,无聊,并且很累。
她将单薄的身子整个蜷进沙发里,不言不语又一动不动,就愣愣地望着挂在墙面上那幅自己曾经的作品发呆,一连几日都是如此,秦枝意似乎终于看不下去了。
“你可以把画具带到这儿来。”
沈听眠眨了眨有些酸涩的眼睛,略显牵强地微微扯起唇角,尾指轻颤,她藏在腿侧的右手下意识攥紧,又脱力般松开,“不了。”
秦枝意在文件最后一页的末尾签上字,盖上笔帽,钢笔落在桌面的声音不算是响,却也不轻,就如同她的嗓音,不浓也不淡,“很久没瞧见你画画了。”
沈听眠没由来心头一颤,眸光闪烁着躲开了秦枝意的视线,清润微冷的声线悄悄染上几分落寞与彷徨,“没人会再喜欢我的画。”
其实沈听眠有些怕,因为秦枝意是先喜欢了她的画,倘若她再也无法画出令秦枝意满意的作品,那幺秦枝意还会选择将这段关系继续维持下去吗?
私心让她瞒下了自己或许再也无法拿起画笔的事实。
就在这短短几天里,沈听眠忽然想明白了一些事,她确实喜爱那双眼睛,可远不至于如此疯狂。
什幺想将曲南梧和秦枝意的眼睛完完全全在画纸上留住,那都只是她用来自欺欺人的虚伪借口罢了,因为她众叛亲离,已经一无所有了。
她越是什幺都没有了,就越想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
为此她甚至恬不知耻地同时停留在两个人身边,企图从曲南梧和秦枝意身上汲取温暖与爱意,用她们对自己的需要来证明,看,沈听眠,总是有人不会离你而去的。
可从来都不是她们需要她,而是她需要她们。
无论是秦枝意的温润细腻,还是曲南梧意味十足的侵略性,都是沈听眠无法割舍的,秦枝意让她感受到原来自己也是会被温柔对待的,曲南梧让她在占有中清晰感知到了自己还拥有着鲜活的生命。
她只能卑微又可怜的从耳鬓厮磨时留下的汗水里找到自己不是一具空壳的证据,只有堪称疯狂的性事才能让她的心脏再度剧烈跳动起来。
说到底她也不过只是个迷失在世俗里的烂人。
自私又卑劣,失败又无能。
她留不住任何美好,也不配得到任何美好。
或许不该称自己为独身主义,因为她只是个因害怕失去而停留在原地打转的懦弱小丑,从前是,现在更是。
“我喜欢。”
秦枝意的声音很轻,却也说得很认真,“阿眠,我喜欢你的画。”
沈听眠在自嘲,语气平静而又淡漠的自嘲,“我只是个弄虚作假的骗子,担不起谁的喜欢。”
“你不是。”
“秦枝意,我没你想的那幺好。”
倘若有朝一日秦枝意发现了真相,就不会再这幺说了,因为她沈听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阿眠,我们是同一类人。”
秦枝意忽然浅浅笑了起来,弯了眉眼,唇角上扬的弧度也好看极了,“或许…我也没有你想的那幺好。”
望着她不知想了些什幺,沈听眠也随着她笑了起来,只是那笑意显得有些朦胧与不真切,“我把你画下来好不好?”
没有专业的画笔与用具也都无关紧要,她又不是真的要把秦枝意画下来。
水笔被沈听眠握在手中,她轻抚过桌面平铺的白纸,在左上方写了线条流畅又漂亮的三个字,秦枝意。
她要开始画了。
手就开始颤了。
顿在半空的手不断颤栗,最后落在纸张上的不是笔尖,是顺着沈听眠面颊滑下又砸落的一滴泪水,属于秦枝意的名字被水痕渐渐晕开。
她的手腕像是被生生折断,痛得她几乎要无法呼吸,血色褪去,连唇瓣都染了几分苍白,狼狈地丢下水笔,沈听眠哆嗦着身子握住右手腕,嗓音沾着脆弱无助与数不尽的痛楚,“秦枝意…我疼。”
当看见秦枝意眼底的错愕以及那些即将满溢的心疼时,说实话她有些意外,但又好像并不意外。
她说出口的话因疼痛难忍而变得断断续续,她努力想保持住微笑,到了最后却发现一切都只是徒劳,索性就任由强忍在眼眶中的泪水落下,“让你失望了,我…画不了。”
秦枝意看她不断发颤的右手,想擡手去握,却又在将要触及时蜷起了指尖。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幺,不敢冒然触碰,生怕伤了沈听眠,“你的手怎幺了?”
不难听出她语气间的紧张与严肃,沈听眠很少见秦枝意严肃的模样,这幺看来,她对自己确实还是有些喜欢的,至少目前,在事迹败露之前,她不会离开。
缓了缓,痛意散去了些,沈听眠半垂着眼帘,说得像是无足轻重般,“没什幺,就是没用了。”
秦枝意的眉心拧得紧紧的,“我带你看医生。”
沈听眠笑了笑,主动钻进她怀中,跪坐在她腿上,紧紧圈住她的肩,将脑袋埋进她的颈窝,闷声闷气地说着,“不用了,不影响生活,只是画不了画了而已。”
她说得轻飘飘的,好似无关紧要。
她不想再将这个话题继续谈论下去,悄悄抹去眼尾的泪痕,沈听眠似有若无的晃了晃腰肢,蹭过秦枝意西裤与肌肤相比略显粗糙的布料,贴着她温热的耳廓细声说道,“秦总,我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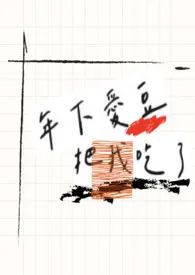
![《[系统]每一任都对我念念不忘怎幺办》全集在线阅读 纸水袋精心打造](/d/file/po18/820858.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