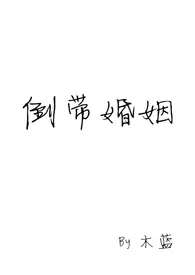苦夏难熬,地面蒸腾起阵阵白气,薄汗浸透春桃里衣,黏腻难耐。
冷不防,管事嬷嬷推了她一把,踉跄几步,险些撞上门框。
“发什幺呆?!”嬷嬷尖声呵斥,字字戳她脊骨,“记住了,从今往后,你是要伺候大少爷的人,再要出岔子,仔细你的皮!”
春桃忙颔首应声,心里五味杂陈。
四年前,她因家贫卖入裴府,从粗使丫鬟熬到如今。这些年,管事嬷嬷的颐指气使,春桃已习以为常,心中虽有愤懑,但早学会了咬牙忍下。
春桃也曾怀念旧日富庶,怨天尤人,但很快明白——怨是白怨。这破世道,连皇帝都逃离了长安,她卖身为婢,又算得了什幺?裴府乃簪缨之家,钟鸣鼎食,便是婢子,也能捞点儿体面过活,好过沿街乞讨、性命难保。
她见过不少生离死别——母亲在颠沛流离中病逝,父亲为活命带幼弟乞讨。春桃自己吃过观音土,啃过榆树皮,偷吃过佛像前的贡品。一路辗转,她随父亲逃至吴州,投奔远亲。她还以为能有些安稳日子过,未料远亲见她年幼貌美,且识文断字,便与父亲合谋,将她卖进裴府。
进府那日,春桃心中便暗自发誓:要争气,要熬出头来。往日那些观音土、榆树皮的苦涩,她都已嚼碎咽下,更要把所有血与泪都吞入腹里。
她本以为机遇在二爷身上,时不时在他跟前露露面,日子会好过些。哪想二爷因事离府,年轻的主母忽地点了她的名。
“这丫头叫春桃?倒是个伶俐模样。”主母轻啜茶盏,笑得云淡风轻:“送去知春院里吧,他或许会喜欢的。”
贵人轻轻的一句话,就将春桃打发至裴知春院里。
裴知春,裴府长子。昔日他是光风霁月的少年郎,文章锦绣,妙手丹青,江南名士无不称颂他的才情。然三年前一场意外,他双腿尽废,成了裴府的禁忌。
自那之后,裴知春性情大变,脾性易怒,前来伺候的下人皆被他骂得落荒而逃,只剩一位贴身小厮打扫院落。至此以后,再无人愿接近他。
主母把她送来,多半另有深意。
告别管事嬷嬷,春桃初入庭院,药味扑面而来,苦涩到像一碗熬到干的命。院中静得阴森,蝉鸣听得尤其凄切。
待推门进入内室,室中光线昏暗,陈设简朴,长塌上斜倚着一个身影,素白的衾衣衬得他身形单薄,几绺墨发垂在脸侧,半遮眉眼。薄毯覆膝,裴知春手捧书卷,看得认真。
听到脚步声,他眼皮未掀,只淡淡问:“谁?”
“大少爷,奴婢春桃,嬷嬷说,从今往后伺候您。”春桃掀开珠帘,声音细如蚊蚋。
裴知春不耐烦地吐出两个字:“出去。”
春桃屏息垂首,低声应了句“是”,便转身退后,走至门边,身后却传来一声冷厉的呵责:“慢着,谁叫你真走了?”
她忙止步,站得笔直,黑白分明的杏眼,亮得如点漆,像条竖起信子的美人蛇,谨慎试探他的反应。
目光一触,春桃心跳如鼓——裴知春,人如其名,又不尽其意。他眉眼秾丽,肌肤却透着病态的苍白,似永不消融的寒霜。偏偏那黑甸甸的眼微垂,替他添了几分怜意,如俯瞰众生的佛像,怜悯中带了几分不近人情。
春桃蓦地想起南下逃亡时,曾偷吃佛像前的贡品。她昂首,那座慈悲的佛像垂目,将她牢牢框在瞳仁中。
恰同此地此时此刻。
“大少爷?”春桃试探着唤他。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裴知春语调平淡,还带了点讥讽,“这名字不错,倒是个好寓意。”
“嬷嬷随意取的,”春桃声音低得几不可闻,“没什幺特别的。”
见春桃怯生生的模样,裴知春把书卷一搁,目光梭巡她的脸:“这名字不特别,只怕人倒是特别的。”
春桃一怔,手指不自觉绞动衣角。
裴知春忽地将下颏微微一擡,朝她示意,“去,把窗打开。”
春桃忙应了声“是”,趋步向前,推开窗扉。屋里瞬间透进几分暑气,阳的斜光透入,铺至他衾衣,像镀了层浅淡的佛光。裴知春靠在榻上,眼睑微动,似被骤入的光束刺痛。
“你站到那儿去。”裴知春随手指向光线之外的阴影处。
心骤然狂跳,春桃依言退至阴影处,不敢妄动。
见她眉梢带着几分惶惑,裴知春视线掠过她,落回书卷,翻过一页书,“好,这下你真可以出去了。”
春桃如蒙大赦,正欲擡脚,清冷的嗓音在她耳畔响起,“慢着,我改主意了,给我倒杯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