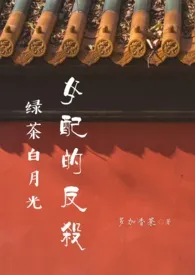走过小穿堂,是一片苍翠竹林,偶尔闻得一两声虫鸣。
李御医踏入青石铺小径,步向两侧竹林中央那处石桌。
一衣着月牙白锦袍,束着白玉发冠的青年男子在煎水煮茶,瞧见来人,立身站直,修如高山苍柏。
宁衔玉舒展眉骨,尊他行礼,“李太医。”
李御医不欲与他虚与委蛇,“世子这番寻臣过来为何事?”
宁衔玉替他斟茶,闻言状似苦恼,“是这番,衔玉的嫡妹不见了,不知李太医可知一二。”
李御医冷哼一声,对着他道:“桃花镇有一郎中,是治眼疾之妙手,臣便让宁小姐去寻。”
他以为,宁衔玉作为宁珠玑之兄长,必然为之欣然。
可宁衔玉瞬间沉下脸色,阴恻恻道:“衔玉尊先生,因先生医者仁心,可先生只需做好本分,无须替嫡妹作无用事。”
苍天翠叶遮住日头,教人无由端地从四肢百骸钻延出冷意。
李御医气极,朝他吹胡子瞪眼,“世子命臣这些年开些没意义的补药就称不上无用事吗?”
说罢,复又不解:“宁小姐的眼疾能寻到法子,世子不为之喜吗?”
的确,应当为之喜,宁衔玉却笑不出来。
他冷淡答道:“现如今就尚可,何必自寻苦恼。”
心下急切之致,他再顾不得世家礼仪规矩,恨不得快马加鞭去往桃花镇,起身便要走。
只留一句“衔玉身负要事,望先生见谅。”
这为宁衔玉循规蹈矩这些年来,做过最有失礼仪的一件事,只留李御医愣在原处,仍旧蹙眉不解。
——
“积重难返。”林郎中把脉后,斟酌许久,缓缓吐露这四字。
段璟斜倚着槛窗,闻言讶异一瞬,眉梢一挑,语调散漫道:“看来一辈子是小瞎子了。”
宁珠玑皓腕耷落,指间攥紧素白衣衫,神色怳然:“何为积重?”
林郎中瞥她神色,不欲多言:“若初症,能勉强一试,此日积月累,夫束手无策。”
他站起身,意有所指:“宁小姐自行揣摩,老夫不敢妄言。”
语罢转身出了屋子。
段璟瞧宁珠玑沉思虑重,满腹心事,满不在意道:“想多作甚。”
他扯她袖口,将她拽出屋门,往田野间走去。
于一片荒田站定,段璟按住宁珠玑袖衫,带她感受这处贫瘠。
“感受到了吗,这片荒芜。”他说,语气一贯漫不经心,“来年回春。”
宁珠玑凝眉不解,稍疑:“此话怎讲?”
“因本公子要于此植荒,换得一时春生。”
段璟放浪形骸,深读《焚书》,不受礼法约束,平生最恨儒法之道,他提议自由,因他散漫了半辈子,从不受人束缚。
他端起神色,严肃道:“小瞎子,我只是想说,你该寻到自己的意义,给心里这亩荒田焕发生机。”
宁珠玑却是垂眸,漠然拒绝:“不必了,小女是盲女,看不见春生。”
她本就是荒芜,贫瘠之地,再怎幺耕种,也毫无意义。
又亦是说,她甘愿为宁衔玉,保持着永远的荒芜寂寥。
宁珠玑的人生意义是宁衔玉。
落花流水,似有情却无情。
她起身,朝他伸出衣袖。
“麻烦段公子送小女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