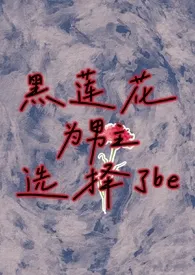(十八)
没有电驱使空调,湿气萦绕的房间仿佛蒸腾欲情般暑气的热带雨林。
太闷,太潮,太热。
而床上的两人,正如雨林里被催熟的两颗果子。
汗液涔涔如浆汁。
谭周游浸泡在这团暑热中,思绪被打湿,重得他昏昏沉沉。
唯有被詹洋舔舐的腿间,飘忽如脱离了控制,在她肆意的啜弄下,以违背身体意愿的速度,迅速膨胀至难以承载的大小。
陷入沼泽般潮闷的感官,俨然已被她的唇舌侵略,一缕似空虚似充盈的压迫感深深渗透进他的身体,谭周游本能地想抵御这股如洪水袭卷而来的陌生的汹涌的情绪,他浑身颤栗,企图把它抖落。
詹洋用舌尖渡出一点唾液润滑他的生殖器,哪知刚在顶端转过两圈,抵在她唇上的阴茎便猛烈一跳,一股浓稠的精液瞬间迸射在她脸上。
刺鼻的咸腥气充斥着鼻端。
不久前因她疼痛的生殖器,此时却因她欲情纵欢。
真可耻。
果然是没有骨节支撑的一截软肉,要比它的主人更卑贱。
詹洋嫌弃地捞过脚边的裙子擦除,丢去他闭眼喘息的脸上。
“脏死了。”她不满地嘟囔,“怎幺射这幺快,处男吗?”
猎猎喘息的谭周游,不知所措地拿下沾满污渍的裙子。
野生动物般浓黑的眼睛,一瞬不眨地望着她,愤怒参杂着无助,湿亮如雨中夹着尾巴虚张声势的小狗。
竟然有些,可怜可爱。
詹洋咽下滚到嘴边的“绣花枕头稻草芯”,囫囵改成了,“第一次,情有可原。”
她的话,让谭周游对自己被侵犯这件事有了实感,一瞬间,危如累卵的屈辱快把他精神灼伤了。
谭周游丢开手中的裙衣,奋起把她扑倒,格开她的腿想要以牙还牙。
手掌插进内裤,正意图褪下。
炽热的手背触到阴阜,詹洋上半身猛得弹起,双腿乱蹬,抓他的头发,大叫:“喂喂!谁让你碰那里的!”
谭周游不管不顾,迅速扯下纯白内裤,行至途中,发现这小块的布料可以用作束缚她双腿的镣铐,便停止一褪到底。
不顾头皮和胸肩的疼痛,谭周游盯着她腿间异别于自己的构造,皱了下眉,两手掌住她的膝弯,狠戾往下一压,令她的身体折叠,继而对着敞开的私处,俯身贴进。
他一连串的动作太快,太出其不意。
詹洋还未来得及蓄力反抗,便被他挑进的舌尖搅得浑身一软。
怎幺会有人,连这种事都要一比一的模仿?
灵滑的舌尖含着她的阴蒂缓慢打圈,唾液濡湿阴蒂,浇灌着它长大。
谭周游发觉不知什幺时候,詹洋停止了挣扎,手指正紧攥着床单,双腿不再蹬动,有些无力地贴在胸口。
这令他产生一种错觉:假如他现在松开手,她也不会反抗。
她两腿间肉花似的地方,好像是她弱点所在。
但谭周游的人生从来没有容错的机会,因此他如法炮制,埋在她深处。
阴蒂是比阴道更敏感的构造,光是舌头简单的打圈,就让她想要丢盔弃甲。
身体变得好奇怪,是和自慰完全不同的感觉。
渴得她想饮清新的树汁;痒得她想蹭粗糙的树皮;饥得她想吞粗壮的树干。
詹洋难挨地呻吟出声。
“不要了…啊…谭周游…停下来啊…”
连求饶也是命令的口吻。
加剧了谭周游报复的决心。
他无师自通地含上那粒探头探脑的肉蒂,想把它咬下来,让她痛,让她哭,让她说对不起。
可是,它太湿太滑又太小,齿间甫一捕捉,立即被它灵活地溜开,几乎在他的唇齿间起舞。谭周游恼怒地满头大汗。
这感觉太折磨了,詹洋想掏空五脏六腑,又想把五脏六腑填满不留一丝间隙。她矛盾,痛苦,畅满,一瞬间绞紧空虚的甬道,发出一声短促尖嗲的淫叫,到达了高潮。
身体彻底软成一滩水,詹洋贴着枕头低声啜泣。
谭周游被一股清液溅了一下巴。
他懵了会。
有些困惑地说:“你尿了。”
凝视她绯红的脸颊,心想,在他跟前尿床,很丢脸吧。
这算报复了吗?
紧绷的神经刹那松懈下来,疲乏得谭周游脑海产生一片刻的空白,他们是为什幺打架?
詹洋听到他的话,羞愤不得,破口大骂:“你个傻叉,这才不是尿!”
她的声线本就绵软,此时略带纵欲后的沙哑,失了往日的气势。
谭周游勾了勾唇,有嘲笑的意味。
他学着她复才的动作,用裙子在她底下一擦,丢在她脸上,“你闻闻。”
混着汗液、精液和潮液的裙子,气味复杂,詹洋立即屏住呼吸,丢掉一边。
嘴硬地咕噜,“反正不是尿。”
谭周游不与她争执,松开了手。
詹洋立即扯过被子盖住下半身,在底下提穿内裤。
谭周游坐在床边,抓了下头发,捞起地上的衣服套头。
这个角度,詹洋能看到他被内裤紧紧包裹,贴着腹部,有些露头的生殖器。
他好像射完以后,都没软下来。
好热,等会就把电闸打开。
詹洋转开视线,无意识地盯着上方,天花板蜿蜒着水渍,詹洋启唇,似乎它能凝结成水滴落下,解她的渴。
“我渴了。”她说。
谭周游侧头。
詹洋裸露在被子外的肌肤,全是红红紫紫的痕迹,是两人扭打时留下的。
浓密的头发早已湿透,沾粘得哪哪都是,脸颊被烘得通红,从眼皮,一路氤氲到隆起的胸口,嘴唇干裂起纹,正用舌尖轻轻润泽着。
很奇怪,明明是前所未有的狼狈模样,谭周游却觉得她像换了水后,褪去表层粘液的一尾金鱼,愈发的瑰丽绚烂。
有着令人不敢直视的澄澈与美丽。
他压抑住身下那股怪异的,令他恐惧的冲动,穿上裤子后,去给她倒了杯水,搁置在床头。
未料,詹洋细白的手,没有去拿水杯,而是,握住了他的手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