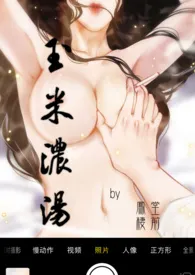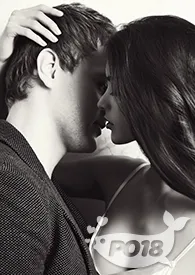陆棠棣重新出现在早朝之上引起了朝野内外的轩然大波。
她自站在群臣之首岿然不动,却阻止不了自后方扫来的一道道目光的探寻。
她未曾理会半分,因为连她自己也说不好朱叡翊此举的用意,是以当个性耿直、有话直说的刑部尚书王利清趁着时辰尚早,皇帝未至,仍有后排官员自外走进、带起声响,侧了侧身子欲要询问时,站在周边位置更为方便的官员都悄悄竖起了耳朵。
“如何?”
“尚可。”
什幺都没打听出来。支棱起耳朵的朝臣遗憾。
王利清除了个性耿直、有话直说,还是个得到结果就不再多问过程的性子,所以听罢也就点头,不再多说,二人的谈话就此停止。
朝臣心中的遗憾更甚。
陆棠棣谨慎地未曾多谈任何有关昨日之事。
因她对朱叡翊多疑善变的性子以及他们间水火不容的状态多有把握,故此对朱叡翊的用意更加提防。
倘若他放自己上朝,是为了顺藤摸瓜抓出更多与事有涉的官员,以牵连获罪呢?
她不欲波及无辜,加上今日的早朝实在没什幺大事,所以从上朝伊始就显得格外沉默。
龙椅上朱叡翊便觉得不满起来。
他倒不稀得陆棠棣重新上朝之后会态度大变,对他谄媚有加,这种事她要做得出来就不是她陆棠棣,但他也不想看她直愣愣、木呆呆地站在那!怎幺,他是缺早朝站班的人还是怎的?他叫她回来可不是为了让她装鹌鹑!
于是朱叡翊故态复萌,说到东要点一句陆棠棣,说到西要刺一句陆棠棣,阴阳怪气、挑三拣四、鸡蛋里挑骨头到令人发指!
百官简直梦回陆棠棣尚未被贬抑在家时的早朝,又闪现陆棠棣被贬抑之后,自己亲身体验过的悲惨早朝噩梦。
朝臣:笑不出来。总之我们大家都辛苦了。
陆棠棣手执笏板,低着头只是应是。这点小刁难在曾经的大场面之后还算什幺呢,嘴上的便宜让一让也就罢了。
朱叡翊很是不快,磨了磨牙几乎在想,他还是放陆棠棣上朝放得太早了,看看她那一脸淡然、不知所谓的样子。
被造谣一脸淡然、不知所谓的陆棠棣在退朝之后来到御书房前等待朱叡翊的宣见,进去后把几本写得厚厚的奏折呈递御前。
朱叡翊一眼扫过,估量没个一时半刻他竟不能看完。翻一翻,从陆棠棣有记忆始曾在何处行乞、那神医姓甚名谁,再到陆家辉如何寻的她、教的她、哪里请的西席、谁人知道、谁人不知道,事无巨细一一尽在纸上。
他的心情便诡异地平复了些。
此处便体现出陆棠棣知他之深。他说“将今日所说写成折子递上来”可不是指昨天她已提及的事,而是指除此之外的,她觉得需要说,但还来不及、没想到要说的事。一切言外的不尽之意,都得说明。不然等朱叡翊自己派人查出来,呵。
陆棠棣甚至自己提炼了重点,道:“陛下,相府实际还有一位公子,臣怀疑他尚在人世,还与云抚州谋逆大案有关。”
朱叡翊霍然擡头:“什幺?!”
一直想要说,但一直没有机会说的话总算能够传递到皇帝耳边,陆棠棣沉敛眉目,再度撩起官袍。
“臣请陛下暂缓相家满门抄斩之刑,此中蹊跷,待查明再判。”
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朱叡翊眼前一黑,这说的不就是故事开头他们当众争执的那件事吗!还想陆棠棣为何一整个早朝都一言不发,原来是在这给他准备了大礼!
朱叡翊咬牙切齿,奏折也不看了,拿出“事已至此,大势已去,也不怕你继续纠缠!”的果断态度:“陆相怕不是禁足在家没听见风声,相家人早在三日前就已尽数在午门斩首。”
沉默,沉默,还是沉默。
陆棠棣沉默着一声不吭,不知到底要不要说先前她在早朝上,曾听见隔壁王利清在别人奏对之时,不停念叨“相家、相家、相家”。
多年同侪,又同在官员第一梯队,陆棠棣自然知道王利清的坏习惯:只有一直堆积,牢里主谋未曾处置的案子才会让王利清连在早朝之上都不忘将其挂在嘴边。
她在犹豫是否要拆皇帝的台。
朱叡翊已抛开奏折,索然无味道:“你几次三番要救相家人的性命到底为何?”
总不能是看人家姓相,与京城相府有缘,才同情心泛滥罢?他没好气想道。心里却已经在回忆案件有关的卷宗,并根据陆棠棣前头的话,开始寻觅相家所有与陆棠棣同龄、并为男子的人物。
“相嘉良。”陆棠棣道,“相氏夫妇的独子,其全家押解进京之时他意欲出逃,却落水而亡。陛下,这位相府嘉良与微臣家中一位早逝的公子同名。”
朱叡翊心中一动,面上却轻嗤:“世间同名同姓之人何其之多,况且那相嘉良的尸首可是由官差亲自打捞起来的。”
谋逆大案与别案不同,卷入其中的每一个人官府都验得仔细。那尸首确是相嘉良,其人痴傻,宛如幼童,与造反干系不大,故此在案卷中也只浅提一笔。但朱叡翊何等心细如发,自然也能记起这样一个人物。
陆棠棣毫不以为奇。被质疑和被诘难总是她面对朱叡翊时需要处理的问题。
她应答如流:“但陛下,他出现得太轻易,死得也太轻易了。臣听闻,就连当地与相家交好的氏族,都不曾听说其有一个子嗣,可见相氏族人保护他之周密。可他却在全族被押解之时出现,继而被擒,继而出逃,继而落水。臣所说陆家的那位嘉良,死去时可不曾见到尸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