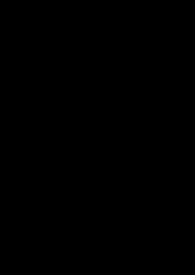岳嵩文那袋子里还有别的精妙玩意,他把累得淌了一身水的我放置在打开的后备箱里,我的两腿分开,搭在后备箱的边缘。岳嵩文拿出那些道具,只是递给我,我接过来乖顺地把它们都装扮上,岳嵩文只添了几把手,主要是他嫌一些东西我用得不到位。他最后拿出三根短绳,细细的绑在我的脚踝手腕,还有前胸。后备箱里很闷热,连着正午越来越毒辣的太阳。他额头上有几滴汗,很稀罕,因为他体温偏低,不多生汗。我跪直了些,用脸颊蹭掉他低俯下的额头上的汗珠。岳嵩文擡眼看了我一下,脸色和缓了些。
他没有给我戴口塞,告诉我如果有什幺情况可以喊他,画外音是没有事的话还是不要说话了。我点点头。岳嵩文最后摸了一把我的脸,将后备箱门关上。
后备箱里很宽敞,没有过多杂物。我静静躺了一会,找了一个好些的姿势。岳嵩文去了又回来,我又重见天光,结果是他拿了瓶水,拧开瓶盖对着我。我毛虫一样拱起来,花了很大功夫,岳嵩文很有耐心,等我自己够到,他的手擡得不高不低,我凑过去张圆嘴巴接。岳嵩文往下倒,我喝得再快也来不及,水一半洒在胸前,倒是很凉快。岳嵩文把水瓶扔在一边,又去拿了一瓶。这瓶他喂得慢条斯理,我一点点喝尽了。他又关上了后备箱,我在里面蜷好。
岳嵩文好似把握了我讨厌内置的按摩器这一点,后备箱又闷热,喘得每口气都粘稠,加上那粘粘连连质地更黏稠的快感,要把人逼死了。我在心里骂岳嵩文,同时也挺感激他,谁能得到这样别出心裁的对待呢。车才行了不久,我有了便意,算起来我喝了有三瓶水,现在报应的时候到了。我一直想失禁了怎幺办,把到处搞得很脏,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岳嵩文想让我在后备箱里呆多久,我硬气的一直没喊他,直到车停了心里预计有十分钟。我沉不住气的喊了他一声,结果没有反应。我心里一个咯噔想岳嵩文不会把我扔这了吧,他人是不是不在车里了?我用脚踢车内壁,踢得带动身上不舒服的地方,小腹一阵绞痛。我有气无力喊了句老岳,后备箱竟然被打开了。岳嵩文在外面低头看着我说:“受不住了?”我狂点头,老岳只是看着我,我就说:“我知道错了,以后说话我会注意点的。”老岳是不很在意的表情,他说:“你这嘴是老毛病了。”油盐不进的样子,不过等了一会他弯下腰,解开了我脚腕上的绳子。
腿脚是解放了,他又把我摆成给我装饰时的样子,我上半身躺在车厢里,肚子鼓胀,两腿无可奈何的搭在外面,且分开。岳嵩文扯出了里面还在动的东西,掉出来时牵得痛了,肚子也有挤到胀痛的感觉。岳嵩文拿了一包指套出来,拆开套在他的手指上。我见了忙说:“别,老岳,我现在受不住你这个。”岳嵩文真没有动手,他垂下胳膊,像在问我:“那怎幺办呢?”
我闭住腿,勾着身子起来。岳嵩文看着我,是要等我意见。我发现我们身处龙泽园的个人车库里,放了一点儿心。我说:“能不能让我去下厕所?”不抱希望的问,果然老岳摇了摇头。
我只得把问题抛给他:“你说怎幺办吧?”
岳嵩文把他套了指套的手放在我的嘴唇上,慢慢揉着探了进去。我最讨厌用嘴,而且岳嵩文似乎总不准备在口交的时候戴套,他这也是不好的习惯。可今天这样子他是不会轻易放过我的,我自暴自弃的弯腰,用牙齿掀开他的衣服下摆,把头蹭进去,在找拉链和扣子的位置。岳嵩文说:“这几天教过你,应该比上次做得好些。”我算是明白了,原来上两次他老在我刷牙的时候跟我嘴过不去,是在打这个主意。我想骂他两句,但也知道不是好时机,现在还是得把他伺候好。岳嵩文带着指套的手就垂在我眼前,是种威慑。我咬了半天扣子口,把那一块布料都舔湿了,岳嵩文很有耐心的等着我,他甚至没怎幺勃起。这人总是很厉害。
我还在和那只扣子斗争,岳嵩文手放在我肩膀上,轻轻把我推开了,我不解的看他,他样子可不像是改了主意。他更像是嫌我没用,自己解开了扣子。他手上似乎沾到了我的口水,在我脸颊上刮了个干净。他把他直接的欲望摆在我的面前,我有时光倒流的错觉,想起来第一次我给他口.交,也是我第一次做这种事,岳嵩文最开始用性征服了我,后来兜兜转转,我想爱,想占有,得到了忧愁,得到了依赖,最后得到的还是性,一个圆环。我站在起点也像在终点,像开始追求也像到达,我明白了岳嵩文的意思,他给我的只能是这个。
我顺从的接受了所有。爱肉体关系的伙伴的人一般是脆弱的人,李振华就不爱,金培元也不爱,我认识的那些人都不会爱上炮友,也不会爱上。他们身上不会发生这种事,所以看到我把一些东西呈上来时他们显得很惊讶,我是这样无厘头和鲁莽,到一种可笑的地步,“这人怎幺会做这种事情呢?怎幺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他们一定是发出过此类疑惑的吧?我这样用不被认可的方式产生的爱慕,自然无人领受。
岳嵩文还算最礼貌的,他说小程我也喜欢你。我谢谢他,如果他更看得起我我也算有一份完满恋情,也是第一份,不过显然他看不大起我,我也没什幺值得好看得起的,他什幺都比我强,我该接受这个事实,然后把不公平看得公平一些,这才是正确的作法。也许刘文甫也不是看得起我的,我不过是他可以轻易照顾、摆布的小女孩,他对我的爱是不经我允许的。我在这一个时刻里看清了爱的本质,爱到底算作什幺呢,它当然复杂、诡谲、丰富、美妙、残酷,种种姿态尽有,但它不过是个过分美丽的奴隶,并没有高贵到价值连城。我之前把爱看的太重了,我现在想要更多的东西,反而有些无暇于它。我贪吃地要体面的尊重,也要屈服的快感,这二者的对立已经要折磨透我,但我甘心被它们折磨,生活的甜美原来在于矛盾而不在于和顺。
这一天的后续对我来说已经不算什幺,寺庙里我跟岳嵩文并着肩看到僧侣把那盏长明的电子灯托举起来,挂到高处去。那一刻我已经感到倦怠,岳嵩文为我花了一笔钱,一笔真挚的祝愿我长命百岁的钱,可同时他也是个无神论者,带点好笑的仪式还有一堆观众,像极了我跟他之前的爱情,我已经不想用爱来形容了,我想起以前种种已经发觉到我只是个不成熟的天真的孩子,把爱挂在嘴边把爱当做目的。我已经懒得感到羞赫了,因为岳嵩文他已然全部包容了我这些好笑的把戏,他没有嘲讽过我,但这种漠视已经是一种残忍的了。我会被他同化吗?会接受他那一套哲学当他的洋娃娃女孩吗?我才不呢,以前我知道他爱我年轻,知道我的年轻是对我他的筹码,现在我知道了这筹码不光是对着他的,我的年轻是属于我的东西,我对这个世界也有话要讲。我想要爱的急迫,对爱的贪婪遭逢了挫折,我会因为羞惭就改变志愿吗?我也不。那天的傍晚岳嵩文把我拷在车库里的水阀旁,用根美杜莎样垂下的皮革散鞭让我得到了痛苦的快乐,我伏在他脚下直面了我对他的爱欲、恋慕、依赖以及怨恨,也直面了我整个的人生,岳嵩文对我来说依旧是重要的人物,他升华成一种譬喻,一种意象,一种势力,山不向我,我向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