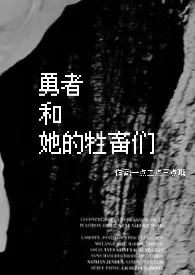那晚到了最后,司徒芊被肏晕在男人怀中。天明醒来时,那还未谋面的主子爷已经离开,留在床上的少女全身都如同被车碾过了一般,双腿之间又痛又麻,因为撑了一夜,两瓣大开的贝肉都合不拢。钟嬷嬷过来检查后,让人拿了温润的药柱捅进去,那药柱虽不甚粗,却也极有存在感,让她时时刻刻都有被继续肏弄的感觉。一旦药柱被花穴内壁融化吸收,丫鬟们便一边啐骂着她的淫荡,又一边再给她捅进一根。
钟嬷嬷说,妇人有妇道要守,她是一只骚贱的母狗,便有犬道要守,她的贱穴日日夜夜总要塞着东西,这便是犬道。
纵是被打击惯了,但每每一听到这些说辞,内心还是一层一层地激起波浪。司徒芊颓丧地躺在床上,双腿整整三天都像硬邦邦的两条木棍,酸涩得几乎失去知觉。但大约是伺候得好,南宫瀚玥一声令下,她的调教便停了下来,得以悠闲地躺在床上养伤。那恶性十足的刁奴碧儿被杖责了之后,听说也下不了床,司徒芊一时倒也过得安稳。
躺了七八天,日日被参汤滋养着,少女的脸色都红润了些。她一身涂抹的都是灵丹妙药,疤痕褪去之后光洁如新,丫鬟上药时嫉妒得眼里飞出刀子来,但也只敢在嘴上过过瘾,不敢伤她分毫。自那日南宫瀚玥突然光临,宅里的奴仆罚了大半,剩下的个个噤若寒蝉。司徒芊被安排住进了沉香阁后,钟嬷嬷便指派了几个丫鬟过来,叮嘱她们,虽不能打,但骂却是可以的,毕竟这丫头的一身傲气得生生消磨尽了,才好做一个任人亵玩的贱奴。
夏日午后闲暇的时间里,监视她的丫鬟们熬不住困,一个两个趴睡了下去。司徒芊紧闭的双眼瞬间睁开,打量了好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地从床上下来,来到最近的香炉前,掀开盖子,飞快地挑起一小粒未燃尽的香料,藏于手心帕中,再盖回盖子,回到被褥之间。
沉香阁,阁如其名,日日燃着沉香,却为求新奇,日日的香都不同。那些香料自是名贵的,却不知兜兜转转,各取分毫,便不再是纯粹的香,而是杀人利器了。
年幼时,她养在安姨娘膝下,姨娘身边有位极懂香料的老嬷嬷,护着姨娘、她和妹妹司徒芸在深沉如晦的司徒府里的安康。那时也是午后,一般少女都恹恹不想动弹,唯有她兴致颇浓地跟着嬷嬷学调香。如今众人都已随着司徒府的覆灭而消逝,那些关于香料的画面却还那样鲜活地留在她脑海中。
她想调的那出香,叫做残烛灭。
想及姨娘,便想到那人世间唯一的妹妹,一行清泪流下,也只有这时,她才觉得自己清醒了些,未曾因那无涯的苦海完全泯灭了自我。
司徒芊抹去眼泪,将冷却下来的香料塞进颈环的凹槽处,她周身赤裸,丫鬟每日也要收拾床铺,却唯有脖颈上以示羞辱的颈环,是不为人察觉的遗漏之处。
她的伤势就快好全了,估摸着那个叫碧儿的丫鬟也差不多能下床了。
这一次,该血债血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