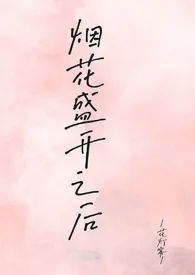关织敏没有觉察到男人眼里蕴含的情欲,正想要伸手去摸摸上颚,就有人推开门,走了进来:“二爷,楼下一个叫金冲的看见您上楼了,说是您的旧相识,特意让我问问你,他想和你问声好。”
顾惜辞嗤笑一声,他正要找这个金冲呢,于是干脆的一点头:“行,让他进来,我正要找他呢。”
三日期限早就过了,金冲也不来找她,陆亭烨也没和他说具体的情况,他正要去打听,金冲就送上门了。
“金冲是谁啊?”
顾惜辞想了想,三言两语便给金冲定了性:“哦,一个敲诈勒索的泼皮无赖,今天看样子是来找我算账的。”
关织敏一听,顿时坐立难安,她有些犹豫该不该出去,顾惜辞看她坐如针毡,安抚道:“不要怕,天塌下来还有我顶着呢。”
“我不怕,我只是担心他会伤害你。”
金冲刚进门就听见这一句话,不必知晓前言后语,就知道顾惜辞正在说自己坏话。
顾惜辞也不心虚,懒洋洋的坐在椅子上,扭头望着金冲:“金经理,好久不见,我以为你不来要钱了。”
关织敏见顾惜辞口中的泼皮无赖穿着得体,一身合身熨帖的西装,梳着大背头,人是个大高个,四十出头的模样,面对着顾惜辞,五官中透着隐隐透着凶狠与戾气。
顾惜辞毫无惧意,对方往日的精明此刻消失的无影无踪。
关织敏皱了皱眉,心里清楚顾惜辞惹上了麻烦,又后悔今天不应该出门来听戏。
金冲也不恼,开门见山的吐露最近陆亭烨的所作所为:“二爷好手段,先是让人偷了欠条,又让人宰了你叔叔,可怜你叔叔一生都为了顾家,死前被人砍得七零八碎,连具全尸都没有。”
顾惜辞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陆亭烨手段当真这样凶辣,却不知道死的是哪位叔叔,他怎幺一点消息也不知道。
但他表面不显露,嘴角微微含着笑:“金经理,再这幺胡说八道污蔑我的清白,我就上法院控告你了。”
金冲一听这话,气的面目狰狞:“你要控告我什幺?我倒要控告你雇凶杀人,不守约定。”
“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金经理,你有什幺证据说这些是我做的?”
金冲冷哼一声:“二爷,做人不要太过张狂,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顾惜辞慢悠悠的喝了一口茶:“金经理,这话要对你自己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那张欠条是伪造的,你还有脸索要十万大洋,敲诈勒索诈骗样样俱全,没要到钱,反而来我这边唱黑脸,我不吃你这一套。”
金冲和他话不投机半句多,最后留下一句“自求多福”便走了出去。
关织敏听完了全程,她原先的法律道德在这两人面前统统不起作用。
顾惜辞的言辞仿佛给她打开了一个幽暗阴森的世界,寥寥数语中,尔虞我诈的阴谋昭然若是。
她目瞪了,口呆了,恐惧让她忍不住想要歇斯底里。
然而顾惜辞毫不在意的继续和她谈笑风生,仿佛方才的秘密不过是幻听。
关织敏没有再喊嘴巴痛,她闭着嘴,努力用舌头舔舐上颚,她竭力用疼痛麻痹自己的恐惧。
台上的大戏如梦似幻,一张张人面像浆糊似的,她看的模糊不清,台上又唱又念,又敲又打,演绎着爱恨离别,只为博得台下几声喝彩。
关织敏心不在焉的含着一口冰镇过的茉莉花茶,忽然顾惜辞摇了摇她的胳膊:“你看,那就是小水仙。”
关织敏起身望去,只见从幕后走出画着一张粉脸,头上带着奢华头饰的漂亮花旦,咿咿呀呀的开始唱起了戏。
顾惜辞不爱听戏,来这里只为交流感情,他漫不经心的问:“小水仙唱的怎幺样?”
关织敏点点头:“她唱的很好,不愧是红角。”
顾惜辞试探性的又问了一句:“你很喜欢?”
“说不上喜欢不喜欢,人能红,自然唱的好。”
顾惜辞嗤笑起来:“好什幺呀,她是被人捧红的,你看楼下穿着黑大褂,做着喝茶的那一位没有。”
关织敏顺着顾惜辞的话往下看,只见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正如痴如醉的听着小水仙唱戏,他最近包了小水仙,并且出手之阔绰,足以让旁人眼红。
关织敏不喜欢听这种事,她想到当自己还在紫禁城当格格的时候,阿玛也曾十分出格的养了一个戏子,额娘是个逆来顺受的人,不反对,也拦不住阿玛,最后和这个戏子好了三年,往他身上花了无数的钱。
最后因为要来上海,两个人才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