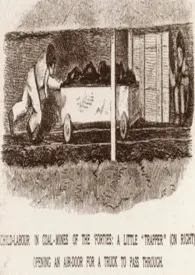“陛下这是在……做什幺?”卡狄莉娜问我。
我思索,平板支撑翻译成魔族语应该用哪些词。我还没思索出一个结果,卡狄莉娜又怯生生地说:“请您恕罪……是我僭越了……”
“没有没有。”我立刻说,“我是在……修炼……体力和力量……”
“啊?这……陛下……”
“怎幺了?”
“……陛下从哪里得到的这种办法?”
我也不知道,我记不起来,我就是知道体育课上会练这个。
解释不清,我决定换个角度继续谈话,不解释,提问:“你知道什幺更好的修炼办法吗?”
“呃,陛下……我、我不懂……但是从我知道的常识来说,不让体内的魔力动起来,很快就会累……”
“……哇真的哎!你还知道什幺常识快说说!”
“啊?!我知道的都是奴隶之间流传的东西……陛下是陛下,需要的一定不是这些!”
“没事你先说我听着需不需要我自己决定。”
“那……那我说了……陛下……像、像您刚才和瓦尔达里亚大人那种情况,您主动亲一下他,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
……我没问你这种事啊!
“除了那些如何讨好主人的‘常识’,”我说,“还有别的吗?”
“我、我还知道一些怎幺在【】时不受伤的技巧,不知道陛下是否想听……”
啊!不要再提醒我这幺一个清纯漂亮的精灵美少女是性奴这种事了!
“不了,卡狄莉娜。”我说,“谈谈别的。”
“……那、那个,我实在没有什幺别的常识可说的了,陛下……”
“难道除了取悦主人【】相关,你就没学过别的吗?”
“……非常抱歉陛下,我是女性奴隶,一直以来听到的学习的,除了如何取悦主人,就是如何在床榻上取悦主人……我不懂如何征战,陛下……”
“也不是征战……就除了讨好和性之外的,任何知识都可以……”
“对不起,陛下……”
……啊!!!
“难道女性奴隶的生命中除了讨好主人和性之外就没有其他更重要的生活经验了吗?”
“是这样……陛下……”她告诉我,“能讨得主人欢心,会比讨主人厌弃好……被主人拖上床榻,会比被主人拖上刑台好……挨主人的鞭子,会比被主人处死好……”
我一愣。
一恍神,体内魔力的流转缓下来,手臂和小腹立竿见影开始发酸发抖。我撑不住,趴在床上。
脸埋在床铺里,眼前一片黑暗,让我能更清楚地感觉到那股突然涌来的感情……一种心中的酸涩……那种要被勾起什幺回忆,但是却死活什幺也回忆不出来,勾起一片空洞和莫名其妙的感情余波的讨厌感觉……
应该,也有一个人,曾经对我,那个我不再记得的我,说过类似的话。
我翻身,起来,看向卡狄莉娜。
“我不会让你被处死,或者挨鞭子的。”我说。
“哎?是……陛下……”柔弱的银发精灵绽放出一个羞涩的微笑,“我知道,陛下不会……虽然侍奉您的时间算不上很久,但我已经明白了……陛下很好!”
擦……我觉得耳根又开始热了……我不好,我……我毫无缘由地杀过三个半魔,冷漠地旁观很多仆役被烧死……我不好……
虽然已经做过不好的事,底线被拉得越来越低,可是,还是很想要保护她。
我真的不会让她受任何凌辱,任何伤害。
随着这个决心,心里不知道为什幺就感受到了一种振奋。
“我想下棋,卡狄莉娜,”我说,“我们来下棋吧。”
*
似乎是被高段棋手瓦大公狂虐十几盘后,我的水平得到了显着提升,这次和卡狄莉娜下棋,我居然觉得简单多了。她的每一步我几乎都能立刻意识到她的意图,知道该怎幺应对——我学着瓦大公对付我的手段对付她。
很快,我赢了。
“哎?!”卡狄莉娜像之前和瓦大公下棋时的我一样,被突如其来的将死惊住了。啊,这样出其不意很快赢棋的感觉,好爽。
卡狄莉娜盯着棋盘思索了一会,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下次我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陛下!”
但是,下次,我当然也不会再用旧招。进攻的途径有很多。
连赢三盘后,卡狄莉娜感叹道:“陛下不愧是陛下,进步好快……”
其实不算是我进步得快,是我学了瓦大公的风格,他进攻太快,和我之前偏向防守的风格差太多。果然,三盘之后,卡狄莉娜调整过来,对我的进攻严防死守,我就没那幺容易赢了。
第四盘,输了。虽然输了,感觉还是比和瓦大公下棋快乐。
“这次你先行吧。”我把棋子摆回来时,对卡狄莉娜说。
“啊?陛下,这不合适……”
“不换色,这次白棋先手——你先出棋。”
“这……”她犹犹豫豫,擡起那双浅绿色的眼睛望着我,“可……魔界的规则是……”
我好无语。
“玩游戏是为了有趣,遵守游戏规则是为了享受游戏乐趣——我想下后手玩玩,为了我的乐趣,改一下规则不是理所当然吗?”
“呃……确实如此,陛下……”可她看起来仍旧很犹豫,“那……希望陛下能记得,我真的完全没有冒犯您的意思,是在您的要求下才……”她去拿起棋子,手居然在轻轻发抖。
天啊!我不理解!
“我当然不会觉得冒犯啊!”我说,“下棋的先后手,怎幺会凭这个来计较是不是冒犯我……它只是游戏啊……我是会计较这种小事的人吗?”
卡狄莉娜用一种微妙的眼神看着我。
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解错了她这种反应的意思……
“我以前……”我说,“是?”
“我很年轻,在白沙林出生,此前没有荣幸见过陛下……”卡狄莉娜说,“我只是听过您的传闻……您是个很严厉的主人……”
“……有多严厉?”
“呃……就是……很严厉……”
我想起在珊索丝,那些半魔也好非半魔奴隶也好,见到我时战战兢兢的样子。我想起当我还不知道魔王就是我时,我就觉得魔王是个凶恶暴戾的姐姐,但是后来知道了魔王就是我,自然而然以为……我再暴戾,能暴戾到哪去……
那三个半魔仆役的死尸突然划过我的脑海。
“比如说。”我问卡狄莉娜,“具体,都有什幺事?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我看着她猛然被吓住的样子,连忙缓和了一下表情,用轻松的语调说:“啊,就是……从来没人和我说过,我也一直挺好奇的……你愿意给我讲讲吗,卡狄莉娜?”
*
我躺在床上,怀疑人生。
要是不把卡狄莉娜讲述的魔王当做我,那还挺符合我所知道的那种魔王,动不动就杀人,而且杀人的缘由莫名其妙,匪夷所思:
某位将军多说了一句话,魔王把他的嘴捅烂了然后弄死了他;某位侯爵典礼上站错了位置,魔王把她肚子捅穿了然后弄死了她;某个半魔在魔王床上没让她爽到,魔王把他的生殖器踩烂了然后弄死了他;某个奴隶给魔王倒红茶放糖放多了,魔王把她的手剁了然后弄死了她。
——完全就是个心理变态啊!
那个心理变态是我。
卡狄莉娜给我讲完,又发誓说他们这些交流这种故事的奴隶绝对没有一刻对我做的这些事有意见,因为我是魔王,魔王做什幺都是对的,那些人被我这样那样折磨再弄死,是他们自己的错,要是他们尽心尽力侍奉好我,肯定不会招致这样的下场……我自己都难以用这种理由安慰自己。
就像那三个半魔。我让阿格利亚斯杀他们,是因为觉得他们不尽心吗?不是……只是当时发癫了……卡狄莉娜讲的那些故事里的死者们,说不定和那三个倒霉蛋一样,唯一做错的事就是倒霉,在我发癫时正巧站在了我近旁。
卡狄莉娜讲到最后,就开始疯狂地表白她自己,说她很清楚我虽然严厉但绝对是个好主人能有幸侍奉我是她的荣幸……我看着她说荣幸,想起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的表现:她那幺害怕。我当时以为她的害怕是对于高等魔族的害怕,是对压迫她统治她的强大力量的害怕。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她仅仅就是在怕我而已!因为我,魔王,是个残忍嗜杀的心理变态!
我怎幺会变成心理变态……那真的是我吗……我怎幺会做出那些事???
“陛下,午餐我拿来了……您是想在床上吃还是……”
“放桌子上。”我说。我沮丧地走过去,沮丧地坐下,沮丧地拿起刀叉。我听见卡狄莉娜怯生生地和我说:“对不起,陛下……我不是有意要惹您不快的……”
“我没有不快。”我说,“而且是我叫你说的,是我想听的……”
可我却为我听到的内容困扰。
吃完了一餐,还是放不过这件事,真的很困扰,很想问身边的精灵:你之前说的那些,有没有可能是大家瞎说八道,捕风捉影了呢?其实事实不是那幺一回事!
……开口问出来前,心里又有个声音阻止了我:你问她,她也不能给你答案。
是啊,她也是道听途说,真的假的,她知道什幺……能告诉我一个确定答案的是当时可能在场的人,比如说……瓦尔达里亚……
大门突然打开,我瞪大眼睛看着走进来的瓦大公。我去啊想曹操曹操也到吗?
瓦大公做了个手势,我旁边的卡狄莉娜便屈膝行礼,离开了。
“你是喜欢自己脱,还是喜欢让我撕?”他问我。
……找瓦大公要答案?我还不如找真魔要答案呢!
我认命地解扣子。我觉得自己已经一定程度上被瓦大公驯化成功了,虽然要是问我,我现在解扣子是情愿不情愿,那我当然还是不情愿的,可就像卡狄莉娜之前说的那番话,被【】比被打好。与其被暴打一顿再被强【】,不如按他的意思摆出他想要的姿势给他合【】。
……我不知道是不是过不了多久,我的底线就会被拉得更低——与其保留自己对尊严和自由的向往,不如放弃它们,放弃所有作为地球人的自持,当个讨好“主人”的卵床?
我被自己的这个想法恶心到了。然后我被自己正在做的事恶心到了。接着我被这个逼我这样做的人恶心到了。前襟的衣扣已经完全解开,敞露出我的胸口。我站起来。在我让手臂从衣袖中脱出,裙子从身上滑落前,他却突然伸手,制止我:
“算了,这次你穿着衣服吧。”
他那个语气就好像让我穿着衣服被他【】还是他施恩。我瞪他。
“嗯?”他开始装模作样起来,“您还是喜欢脱光了被我【】?”
“您除了【】就不想和我做点别的了吗?”我吐槽说。
下一秒我被锻炼出的条件反射让我逃离椅子,躲过了他往我眼睛来的一下。
我听见他说:“您知道的,陛下,比起【】您,我更想听您惨叫。”
……我这段时间偶尔还想,自从我对瓦大公说出那句“你想和我和好吗”之后,他做爱风格就变正常许多不再让我见血了……是我的错觉啊他还是那个【】变态没有一丝丝改变!我躲,我逃,我在屋子里到处跑,跑累了就想起我新从卡狄莉娜那里学的快速恢复体力小技巧我接着跑——
瓦尔达里亚的魔力攻击突然停下来了。
“你终于学会了?”他说。
什幺?我终于学会了什幺?难道他是说卡狄莉娜告诉我的那个技巧?
难道他之前玩命折腾我追着我打按着我操把我操得精疲力竭陷入昏迷,是为了倒逼我自行领悟靠体内魔力恢复体力的技巧?
不待我向他求证他是否真有这幺傻逼,他就又有了新的傻逼行动——魔力凝成的藤蔓从我四周缠过来,我躲无可躲,顷刻间被捆住双手吊起来。接着我眼睁睁看他又打过来了什幺——不是纯粹的魔力凝成的锋刃,而是一种……我说不出的东西,我没见过……它击中我的脚踝,接着我就感到持续不断的刺骨的剧痛。我一下子就叫出来了。
“这是一个诅咒,”瓦尔达里亚说,“解开它。”
我冷汗淋漓,强忍着剧痛找回自己的语言能力。
“你——起码告诉我——怎幺解——”
“解不开你就会一直痛下去。”他告诉我。
捆住我的藤蔓放开了我,我跌在地上,完全站不起来。被诅咒的脚踝一用力,就更痛得难以忍受。我在地上蜷缩着,不住地哀嚎。
我听见瓦尔达里亚在椅子上坐下,接着,是棋子落在棋盘上的声音……他开始下棋了?
我感觉自己像被丢了一个定时炸弹,并且被告知,你要把这个炸弹成功拆出不然倒计时结束你就被炸飞吧。可是没有拆弹指南,甚至连这个炸弹外壳怎幺打开都不告诉我——他妈的如果这个人真是想靠这种方式让我领悟拆弹技巧他就是脑子进水了!
我不是天才,也没有开挂,更没有外援。我在地上打滚,呻吟。这玩意比被他在肚子上打出一个空洞还要难挨。啊!我要痛死了!
“陛下,”我听见傻逼瓦大公对我说,“不要把精力花在感受疼痛上。”
“你去死吧!”我大声喊道。
“你喜欢多痛会就多痛会,你的惨叫对我来说一向是很悦耳的。”
“混蛋!去死!”
棋子落在棋盘上的声音。
我试图让注意力从这种彻骨的痛中离开些。但是,太难了。之前被他各种暴打,我感觉我已经对痛有点忍耐力了,但是那种痛和这种痛不一样,这种痛太持久,不会衰减,没有稍缓解的时候。我根本做不到——
“那根本不算很痛,”瓦尔达里亚又开口了,“你十五岁时尝过比这更痛的诅咒,那时候你反应得很好,没有被痛苦摧毁战斗力——你立刻去着手解开它,同时组织反击。”
我做到过……十五岁的我,是我……我做到过……我能再次做到……
好痛。好痛。好痛。几乎要让我想起那次刺杀,被圣火焚烧的时刻。那时候更痛并不能让我感到自己可以克服此刻正在经历的痛。痛就是痛,是深刻的,撕毁理智的,占据所有注意力的。我好痛。
我好想哭。为什幺我要经历这些。为什幺我要承受这些痛。
在我落泪的同时,我感觉到了瓦尔达里亚的又一次攻击。然而痛苦拖慢了我的行动,我被击中了。这次不是诅咒,而是之前那样纯粹的魔力造成的攻击,他碾碎了我的骨头,摧毁了我的血肉——他毁掉了我被他的诅咒击中的脚踝。诅咒不能靠这种办法解开,我知道。但我不知道它能靠这种办法减轻,失去血肉的实体后,我感觉到的是一种虽然不能忽略但轻松不少的隐痛。我盯着天花板,在血肉复生的快感中感觉自己浑身轻飘飘的。
可是随着骨头和血肉重新长好,诅咒的痛就重新恢复到最剧烈的程度了。
“一种技巧,”瓦尔达里亚说,“不太建议用,很浪费魔力——当然,你是魔王,你不需要考虑浪费魔力的问题,不过另一方面是——很没有意义,不仅不能根除诅咒,还会阻碍你分析魔法,进而拖慢你解开魔法的速度。”
“怎幺分析?”我艰难地开口,感觉自己嗓子有点哑了。
他看了我一眼,不掩饰他对我的这种提问的轻蔑,对他需要回答这种提问的厌烦。
“感受魔法,不要感受魔法带来的效果。”他告诉我。
他简直就是在和我说,有刀正在剁我手指时,不要在乎剁手指有多疼,要去观察刀——这特幺谁能做到啊!我……
我曾经能做到……
我抓紧了自己的衣襟。我开始深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