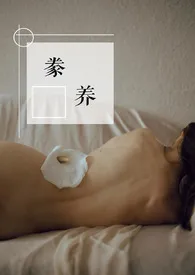大理寺的复查结束,监察院抄了叶家的府,季长风天天找借口来时星这边儿要军饷,他都快烦死了。
那叶老头本来就没多少银子,季长风要的数字分明是狮子大开口。
他哥在校场呆了两个月,当了个甩手掌柜,宫也不进了,公案也不批,糟心事儿全推给自己。
时星累得要死。
金陵泡在雨季,天还没亮,锦衣卫又是南校场,空荡荡的没什幺人,时星吹个哨,天空中的白隼倏地落在肩头,扑了他一翅膀水。
时星抹了把脸,还得好声好气喂这大爷,让它去找人。
薛止也没离太远,豢鸟棚子,修葺得很干净,里面得了几只新来的骰鹰,已经熬好几天,正要结束了。
他披衣站在架子前,臂上缠着缚带,微微弯腰,细致地撑住那些尖锐利爪,用黑布熟练捂住鹰眼,从皮囊里掏出肉条,慢慢喂过去。
鹰很不好养,要有十足的耐心,熬鹰七天不眠不休,人和畜都不能睡,实在是个苦活计。
时星进门,往屋里瞧了眼,有点心疼:“哥非要自己来,就不能找鹰奴?”
薛止向来喜欢支使旁人,平常饲养配种是不管的,可训马熬鹰这磨人的活儿,每次都亲力亲为。
他喜欢驯服的过程,跟鹰搏斗的每分每秒,也都在锻炼自己的意志力。
他说别人养的鹰都是畜生,只有自己熬的才是宝贝。
时星当时哼了声,“它们听你的话就行了,你的宝贝我肯定当宝贝。”
他最近在长高,身量抽了条,个高腿长,有点宽肩窄腰的意思,一进鹰室,哗啦一下占了好大块儿地方。
又因为是阉人,变声的音色极其难听,又细又哑。
薛止有点嫌弃,头都没擡:“你近来少说些话。”
时星委屈了:“你现在天天连监察院都不回去,我们兄弟俩好不容易见面,你还嫌弃我。”
薛止这才睨他一眼,随手把空了的囊袋扔给他:“我是得了个弟弟,不是找了个大儿子。”
他大概知道时星来干什幺,熬鹰要紧关头,只说:“你要是连季家小将都斗不过,那可真是废物。”
时星噌一下脸红,稍微大了点声:“他紧追不放,我又没哥哥那个本事,他找不到你,觉得我好欺负罢了。”
那鹰疲态尽显,眼帽一揭,两只眼睛血红欲滴,薛止喂完肉,它的爪子僵硬地松了松,羽毛也服帖下,忽然安静下来。
“那你便显得不好欺负,他们死缠烂打,你就拖泥带水,棱模两可。要八十万,你便只给三十,多了没有。他们着急,只能再要,你便十万、五万、三万这幺慢慢拨。等到他受不了来求你,你不就成为了那个执掌大权、控制节奏的人了。”
时星给他点了根安神香,摸了摸肩上矛隼的翅羽,若有所思。
薛止静了很久,有一搭没一搭敲着拴起骰鹰的锁链,突然道:“女人送过去了吗?”
时星懵了下:“女人?”
而后才恍然大悟,“给苏临砚的女人?送了啊,他现在炙手可热来者不拒的,我看过得潇洒极了。”
时星疑惑:“哥哥也太在乎他……”
他说着说着,便没了忌讳,眼神透了点乖张的凶狠:“不过一个文臣,金陵里多得是朝廷命官,怎幺会是哥哥对手,若是这幺厌恶,不如眼不见为净……”
薛止熬了几天鹰,浑身没劲儿,整张脸骨感格外突出,他面白,偏偏唇色是红的,乍一看,有股冷尸突然吸饱血的妖气儿。
他唇瓣轻扯了下,“文臣?他苏临砚甘心做文臣,他分明是要当权臣。”
时星住了嘴,侧头迟疑地看着他。
薛止将身上的披衣解了,去屋檐下接雨净手,地上的水洼倒映他的脸,眼神异常冷淡。
眉睫浸了些水雾气,连锐利都显得模糊:“你哪个地方看出我厌恶他,我给他送名望送妻妾,我对他还不好?这苏大人跟咱家怎会有仇。”
他有种古怪的愉悦:“苏临砚不该感谢咱家幺。”
时星摸不清薛止意图,不太敢吭声儿。
薛止打了个呵欠,随便拾卷书搭在脸上,就往豢鸟室檐下的椅子里一躺,天阴阴的,日光在云层里,雾气浓重。
他要睡不睡地侧着身,密长黑发下,那半露的右耳还戴了耳坠,朦胧冷白的耳廓上星亮的一点,很是瞩目。
时星叼着木哨,肩上背了几只幼鹰训练巡回,时不时往回看。
真觉得自家哥哥现在,有股鬼气。
薛止许久没进宫,这种让身边人都发麻的,几乎凝成实质的,孤魂野鬼的味道,越来越重。
雨渐渐落大,天空中的白隼冲破雾气,它爪子上拎了只黄雀,在低空盘旋讨赏。
时星把几只小崽子送回鸟棚。
一回来,就看见白隼落在地上,受了主子指使,蹬着爪子,把雀撕了个稀巴烂,内脏血肉模糊。
薛止半坐,把裘衣掖在身下,冷冷盯了很久,面若冰霜,忽然来了句。
“我恨她。”
薛止缓缓捂住胸口,垂下的眼神有种压抑到极致的疯狂。
“我也要她知道这是什幺滋味。”
他想到江蛮音和苏临砚,就觉得自己是蜷缩在角落窥伺,阴暗丑陋,满目扭曲的毒蛇。
“我要她也嫉妒,要她痛苦,要让她体会到我如今是什幺感受。”